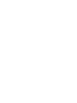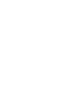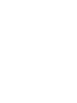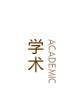对话历史 重构经典——郑济炎及其画作印象
2017-08-27 01:58:00来源:常熟美术馆点击:11010
夏淳(常熟美术馆副书记兼典藏研究部主任)
任何一位有理想的艺术家,都必须既置身于历史的参照系中,从艺术本体论意义上衡量自己的价值所在,又需要投身于当代的试金石中,通过社会学效应来检验自己的现实意义。故而,确认这样的认识可能有助于我们寻找到相对有效的切入点去理解一位艺术家和他的作品,这也是我在谈论郑济炎先生和他的艺术时想要表明的基本前提。
众所周知,郑济炎先生是一位擅长中国古典著作人物画的优秀画家。他早年曾学艺于常熟本邑陈之祥、唐瘦青两位画家,但对其作品风貌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后来的恩师,海上名家刘旦宅。当我询问起他与刘先生结缘的经过时,郑济炎却非常坦然地告诉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伴随着国内外文化交流与产业的复兴,他原来所在的工艺美术单位出于培养人才和商业市场的需要,将其引荐给刘旦宅,以便能够进一步学习中国画。这让我想到了著名美术史家高居翰在探讨明代绘画时,曾提醒我们注意书画家的不同生活形态与他们作品风格间的相互关联。高居翰站在“分类论”的立场上举例说明了沈周与吴伟所选择的画风因四周及自身的期望和不同的社会角色而无法互换,甚至认为这种影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而,我们固然可以说一位画家的艺术趣味主要来源于主体因素,但也必须承认类似于郑济炎先生的艺术道路仍然受到很强的外在规约。
而就中国人物画的本体化进程来看,晚清以来至少经历过三次重要的转折。一是清末,以任伯年和钱慧安领衔的海派人物画重拾因文人画大兴而被遗忘的造型技巧,以便能够应对新兴的市民文化趣味;二是民国年间,由古今与中西之辩所引发的人物画复古(主要转向宋元,乃至晋唐)与改造热潮 ;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物画再次成为“成教化,助人伦”的政治工具,得到大力推广。但无论哪一阶段,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大局从形态学角度出发都以“写实”为重要特征,从价值学原则来衡量都以对传统文人画的反拨为旨归。在这其中,主要成长于新中国的刘旦宅,却以连环画创作的专业背景,通过古典著作人物画这一较为折中的艺术样式一方面将人们喜闻乐见的经典题材转化为形象准确、神态生动的唯美图式,另一方面又显示出迂回绍述传统的特性,最终使他成为较早摆脱时弊的少数中国画家之一。明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直承刘旦宅衣钵的郑济炎先生的艺术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郑济炎先生艺术创作的成熟期毕竟处于更为开放的现实情境中,坚定地恪守某一绘画样式,必然有其自身的思考。但我们仍应注意至少两方面的文化逻辑。一是传统的时代号召力时常迫使一部分画家回归经典,尤其是在晚清以来,以钻研书画、篆刻、诗文并坚守文人画图式笔墨纯粹性的助力下,直到新世纪,常熟的画家集群依然保留着对传统的崇敬之情。虽然无法再用“南宗”和“四王”要旨来加以概括,但至少“不求奇峭”的画风还是占据着重要位置。透过郑济炎先生秀逸、含蓄的笔墨,也总能让人感受到与明清吴地绘画一脉相承的精细与文雅,感受到他谦逊温婉的个性。其次是经历了现代文化洗礼的画家当遭遇到更为多元与复杂的现实境遇时,努力构建自身与过去联系的冲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强烈。就像郑济炎先生自己所说:“抛开世俗之纷扰,静静地与古人对话,虽然相距千年,总感到血是相通的,意是相连的,在与优秀古人的情感交融中,思绪趋于静化,境界得于开拓,人格达到升华。”这种试图与先贤建立联系的怀旧情节正是在社会文化发展发生剧变,传统生活事物快速消失的当下普遍出现的精神现象。
在郑济炎先生众多作品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历时十多年创作完成的《宋人词意图集》。如果说,他的这类作品可以简略地概括为“形神兼备,雅俗共赏”(萧平评语),那么其实质还在于画家既需要有效地完成对文本的图解,创造出通俗化的视觉接受,又需要超越文本的语义发挥,营造出“意在象外而风韵嫣然”的艺术效果。然而,自词意画诞生以来,伴随着中国画“诗画一律”的美学要求,无论是对中唐画家张志和《渔父图》的记载,还是宋元以还,以词题画,以画状词渐成风气,抑或明末《诗余画谱》的刊刻乃至晚清民国更大范围内的大众化需求,词意画中再现词意远多于重造词境的现象却普遍存在。但在郑济炎先生的笔下,依托全面的技术才能和对文学的出色理解力,尚再现与重表现得到了有效调和。他的人(尤其是仕女)与物,总是以传统的标准图式为基础,弱化个性化的品格呈现,追求特定的审美表达,以此来满足词意与画意、经典与通俗之间的相互匹配。委婉的情韵、错落的美感都使他的作品与宋词长短参差的特殊体式和婉约深曲的艺术风格之间形成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另一方面,郑济炎先生又善于运用不同的外显与内隐方式,借宋词发挥其与画之间互释的“形象性”链接和互补的“象征性”链接,使词境与画境相映而生色,努力寻求“诗画一律”的内外圆成,他的作品也由此避免了此类题材容易带来的浅尝辄止,达到了折中和谐的艺术境界。
不过,由于文本的限制以及人物画本身存在再现性强,因而易成 ;表现性弱,因而难工的特点,使得历朝历代的画家都面临着主体情感表达和艺术创新的巨大挑战。所以,不管是郑济炎先生的《宋人词意图集》还是他的其他古典著作人物画都只能被动地将自我部分让渡给他者,以求在更严格的法度与情感之间获得巧妙的平衡。这看似是一种损失,但在我看来,却有望获得新的收获。因为当身处时代浪潮中的观众在面对这一类型化题材时,显然会将不同的个体文化和记忆带入作品,观众也就不会是当下无“先见”地进入历史,而是当下的“阅读视界”与“历史视界”之间的一种“视界的融合”(伽达默尔语)。在这种融合中,历史以及个体与历史的关系都被重新建构起来。在客观的时间距离和主观的心理距离影响下,郑济炎先生的作品成为引导我们想象地介入历史且虚幻而又真切地体验历史的重要工具。当下的这种感受也与以往任何时期都存在明显差异,在一个信仰与偶像普遍缺失的年代,传统主题的严肃性和永恒性不仅能够带给人们强烈的审美震撼,同时也贯穿着对道德力量、伦理意识和价值体系的重拾。故而,郑济炎先生反观传统、追溯师承的审美追求与那些中西兼参、古今同修的绘画理念一样具有反映时代面貌的文化价值。
最后,我想表明的是,我与郑济炎先生的接触甚少,对其艺术的了解十分有限,加之才疏学浅,为其撰文,恐难中肯。而时至今日,任何执着于简单的立场和固定的视角去解读一位艺术家和他的作品都可能带来执者失之的后果,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艺术所呈现出的模棱两可、变动不居等特性更使人们对它的评介不再具有惯常意义上的精确指向,有时甚至莫衷一是。诚然,作为一位画家,已是古稀之年的郑济炎却依然精神矍铄,勤于笔墨耕耘,对艺术的执着令我倍感钦佩,诚如他所言:“生命不息,笔耕不止”,我想正是这样的坚守让他的作品有望超越当下的时空,辉耀于更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