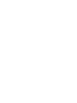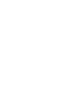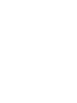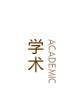中国150位巨匠--庞薰琹
1997-02-01 02:04:00来源:庞薰琹美术馆点击:6829
作 者:周昭坎
出 版 社:台湾《中国巨匠美术周刊》中国系列
出版时间:第127期
中国现代美术的先驱庞薰琹,字虞弦,笔名鼓轩。 江苏常熟人,出身于书香门第。
江南水乡淳朴爱美的民风给予庞薰琹最早的艺术启蒙。民间刺绣的图案,枕头、帐幔上的朵朵绣花,姑娘、妇女头巾、围裙上的装饰纹样,都使他产生浓厚的兴趣,掺进自己的想像加以描绘,十岁时,便能画些工笔花鸟画。但是,为了摆脱旧家庭的束缚,他进了上海 震旦大学预科学医,只是仍然迷恋着绘画。然而,学校里的外国神父的一句话:“ 中国是出不了大画家的!"却使他毅然离开这所大学,去跟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古敏斯基的俄国人学油画。
民国八年(1919)发生的五四运动,激起青年们到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潮流。满腔热血的庞薰琹不例外,于十四年(1925)远渡重洋到巴黎学习艺术。先进敘利恩学院学素描,锻练造型能力,过一年,又进格朗·歇米欧尔研究所深造。他一方面从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法国古典派艺术进行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目接巴黎五光十色、扑朔迷离的现代绘画诸流派艺术,体味领会、进行探索,对毕卡索敢于不断改变自己作风的气魄和才华,大为倾倒。但是,当他挟着自己的创作,到巴黎一家艺术家经常聚会的古堡咖啡馆,去请教一位法国著名的批评家时,那位先生连他的作品都不看一眼,只问他对中国民族艺术有没有研究过?他回答说没有。这位批评家便说:你先回去,研究了你们祖国的传统艺术之后,再来法国,我再看你的画。批评家的这一席话,振聋发聩,使庞薰琹下了回国的决心。民国十九年(1930)他回到故乡常熟,开始钻研中国画论、画史,并和西欧美学思想进行对比,写成《薰琹随笔》,连续发表于《艺术旬刊》,记录了一个画子从东方走向西方,又从西方回归东方的种种思绪、体验和心得。
是年秋,他定居上海,创办“ 苔蒙” 画会,希望通过画会树立一种有独创精神的新艺术风格。次年,他在上海昌明美术学校任教,自己也办了一所画室,然后,又就聘于上海美专西画研究所为导师。当时,他非常看不惯那些依靠官方而自称的所谓画家,他们或师古不化的因袭,或唯西方绘画是从,毫无艺术气质。因此,民国二十年(1931),他和志同道合的倪贻德、王济远、张弦、阳太阳、杨秋人、周真太、段平右、曾志良、陈澄波等组成著名的新美术团体“ 决澜社” ,决意掀起一股与官办画会抗衡的新兴美术运动的狂澜。决澜社的《宣言》疾呼:“ 我们往古创造的天才哪里去了?我们往古光荣的历史哪里去了?……我们再不能安于这样妥协的环境之中,我们再不能任其奄奄一息以待斃;让我们起来吧!用那狂飙一样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我们以为绘画决不是宗教的奴隶,也不是文字的说明,我们要自由地、综合地构成纯造型的世界。……我们要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兴的时代精神……” 。
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庞薰琹奔波于杭州、上海,举办了四次决澜社画展。他的《地之子》即展出于第三次社展中。由于决澜社的展览,把鄙视和嘲笑掷向政客、巨贾和他们豢养的“ 官学派” 画家。因而遭致攻击、恐吓和通缉,决澜社只存在了短短的四年。但决澜社和庞薰琹对于介绍和研习西方现代绘画,推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留下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影响。
这一段时期(1930-1936年),也是庞薰琹立足本土,入流现代艺术潮流取得重要成果的阶段。他的一大批作品:《籐椅》、《裸女》、《屋顶》、《绿樽》、《在画室中》、《地之子》、《无题》、《人生哑謎》、《如此上海》、《如此巴黎》等,成为我国早期现代艺术的代表作,展现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形式和精神。遗憾的是由于社会的动荡、时代的变迁和个人的遭际,庞薰琹中断了这种具有时代精神的现代艺术的探索,转而把精力集中于工艺美术方面,尽管他于这方面的努力,最终为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建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教学体系,但对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
庞薰琹在法国留学期间,适逢十二年一遇的万国博览会的举行。外国工商美术的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即已萌芽了将来一定要建立一所中国人的工艺美术学校的理想,并且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回国以后,他曾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创办了“ 大熊工商美术社” ,举办了一次“ 工商美术设计展览会” ,开展广告和工艺美术设计业务,但却因外国广告公司的排挤而不能立足。因此,二十五年(1936)他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时,说服校方开设“ 工商美术课” ,企望培养出一大批足以与外国人竞争的装潢设计人才,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工艺美术体系。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南迁,计划落空。
民国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38-1940),庞薰琹在云南昆明担任中央博物院研究员,致力于民族工艺美术的研究,在云、川各地考查研究了大量古代陶、铜、石器工艺图案纹样和少数民族服饰图案,编绘了《中国图案集》四册和《工艺美术集》。三十年至三十六年(1941-1947),他先后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和中山大学任教。从事工艺美术教学,编绘了《工艺美术设计图案》。期间,他曾于三十年和三十二年(1941和1943)在成都、重庆举办四次个展,分别展示他过去的创作和后来多用毛笔画的少数民族题材和唐装舞女图,风格各异。
1949年后,他先后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杭州)和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3年,周恩来委托他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全力以赴,组织力量进行社会调查、收集民族、民间工艺美术遗产,进行整理、研究、展览、出版,并到苏联进行考察,终于用他的辛劳和汗水,于1956年建成中国第一所多学科、综合性的高等工艺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出任第一副院长。但不久,即于1957年“ 反右” 运动中蒙垢成为右派分子,被解除了副院长职务,除教书外,闭门著作,历20年写成《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直至1979年平反,至1980年恢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职务。从1949年到1972年,23年中他仅画了《鸡冠花》等5幅小油画,1973年才开始重新执笔画些花卉作品,有油画也有国画,装饰性和绘画性、写实和写意融为一体,清新淡雅,但却流露出“ 超脱” 的寂寞,已经迥异于四十多年前“ 前卫” 的庞薰琹了。
1985年3月18日清晨,庞薰琹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9岁。
庞薰琹早在巴黎时就对工艺美术的图案设计感兴趣。回国后,收集了上千幅中国古代青铜、陶瓷、丝绸和漆器上的纹样,并于此基础上在四川郫县创作了一本《工艺美术设计》,1944年交友人带到国外出版,辗转三十余年后,由英国美术史论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带回北京交还庞薰琹,198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四幅方盒图案设计是1940年在昆明创作的《中国图案集》100种设计中的四种,也是以古代纹样变形手法设计,曾在昆明展览,获学术界高度评价。
青年时代的庞薰琹激烈地反对刻板机械地模仿“ 自然主义” 和所谓“ 写实派” 的绘画。他认为这种模仿自然的绘画,在现代“ 以数秒钟的时间拍一张照相,不会较描写数个月的一幅少真实。” 由此,他主张艺术家应该利用各自的技巧,自由地、自然地表现事物和自我。他的艺术主张,在《决澜社宣言》中更表白得十分明确:“ 我们厌恶一切旧的形式,旧的色彩,厌恶一切平凡的低级的技巧。我们要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时代的精神。……野兽派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 达达派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二十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出现一种新兴的气象了。”
1932年前后创作的《如此巴黎》、《如此上海》、《人生的哑謎》、《画室内》和1938年创作的《路》,有别于同时期创作的《地之子》、《三个女性》那种沉静的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力图用激烈的绘画语言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绪。用庞薰琹自己的说法是“ 我的一生,是探索探索再探索的一生。” 他一直在尝试用各种手法表现不同的主题。
在《如此巴黎》这幅作品中,画家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形象,用“ 蒙太奇” 手法剪辑,以现代构成方法处理构图,将繁华而疯狂的夜巴黎浓缩在一个画面上,卖笑的女人、赤裸的身体、愁苦的眼神、叼雪茄的男人、隐现的警察、摇曳的灯光、眩目的广告,便是一扇门、两扇窗和几张纸牌,也在时刻变幻着。
《如此上海》、《人生哑謎》采取了相同的手法,表现了类似的内容,可以认为是画家于这一时期思考社会现象的一组系列画。这组作品的表现手法虽然未脱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影响,但是,在形象、色彩方面具有装饰性,显然较为接近东方人的审美情趣,错综复杂和组合却不失谐和自然,激烈变幻的表现却不失平衡合理。
庞薰琹在年轻时代,尝试了西方绘画各种流派的画法,最后选择了从西方回归东方的艺术道路。他在尝试各种新画法时,并不是简单地模仿抄袭,而是溶入了他自己对描绘对象和适合这一对象的表现方法的理解,所以,他的用笔自然、流畅、没有造作的痕迹。这幅《籐椅人体》是他最得意的一幅早期作品。虽然是一幅学习马蒂斯风格的习作,但其神韵不失大师风范、简炼到多一笔即为添足的线条、洒脱流畅;夸张的变形也是到了极致,头部的大小尽管和腿的比例失调,但是,再大一点或者再小一点,这幅画就没有美学价值;籐椅的黄色和人体的肉色非常接近,同样也是调色板上多一分别的颜色配比,就会失去这种和谐的对比。这幅画过去很少有机会与读者见面。因此特地介绍。可惜原作已不复存在。据画家的女儿庞涛(也是一位著名女画家),抗日战争爆发时,从北平带出的一卷三十年代的作品,总共有20多幅,这一幅也在其中,而现在祇剩下了《法国老人像》一幅。
这是庞薰琹有感于当年江南大旱,土地龟裂,民不聊生而花了几个月时间创作的一幅作品,本是一幅油画,曾于1932年他在上海举行的首次个人展览及在第三次决澜社作品展览中展出,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展出时曾轰动一时,但后来被当局认为有“ 赤化宣传” 嫌疑,受到攻击,他本人收到匿名恐吓信,不久,法租界巡捕还准备缉捕他,他在傅雷的帮助下逃到了杭州躲避。据说这幅画后来由四川博物馆收藏,但又转手一家外国博物馆买去。现在这幅是1934年用水彩画复制的,原作也已散失(编者注:水彩画原作现藏庞薰琹美术馆)。
画面上是一个将死的僵硬孩子,横卧在一个农民模样的男人手中,这个男人一手扶着孩子,一手握拳;孩子的母亲俯首靠在丈夫的肩上,掩面而泣。他们穿戴整齐,看上去体质健康。据画家自述,他是用这对健美的青年夫妇来象征中国,而用将死未死的孩子隐喻当时的中国人民。
无疑,画家是充满感情完成这幅油画的。据说,他回到常熟家乡,亲眼看见农民把地契贴到地主的大门上,便全家离乡背井逃荒而去,庞薰琹含着同情的泪水创作了这幅画,他试图采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来创造一幅主题是中国总有一天会摆脱贫困的作品。
我们注意到画家创作的是一种被压抑而又平静的人物情感。他采用简化和拉长了的形体描绘,大面积平涂,以平面、装饰的风格来表现朴实和力量,十分成功。这种风格不由使人联想到毕卡索蓝色时期的作风。画家承认他最佩服的就是毕卡索。但他决不是模仿和照搬。他主张“ 中国学术现代化,外国学术中国化” ,他吸收外来形式,却注入了中国人的情感、神韵,包括造型的线条的运用。可惜像《地之子》这样具有时代博大宏伟精神和深刻内涵、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作品并不多见。
在庞薰琹的作品中,有几幅以他生活历程中关系重大的几处住处景象为题材所作的风景画,是反映画家真实心情的精心佳作。这幅《白家庄旧居雪景》,有人认为是画家政治上蒙冤后所作的第一幅作品,阴冷、 滞凝、沉重的情调,反映了他被免职后打发到东郊白家庄两间斗室离群鳏居的忧愤、委屈、迷惘的心情。
其实仔细分析这幅画面的情调并非如此。厚重白雪覆盖的新兴城郊,虽然冷清,但一片微弱温暖的阳光映照着新建的住宅,如同同一时期画家在白家庄斗室里画的那些花卉,透露出的是一样的乐观和富有生机。庞薰琹本是一个乐观豁达的艺术家。当他刚搬到白家庄时,固然因为蒙冤、妻子丘堤去世,使他一月间黑发全白,病至垂危。但经一位老中医点化,知医药无效,全靠自我解愁,于是拿起搁置画笔开始画花,心情逐渐开朗,病渐痊癒。1962年,他又与袁韵宜女士结婚,领一女,生活重新有了信心。因此,他那时虽因作为“ 摘帽右派” ,担任教学工作中仍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发生,但心情上总还是乐观的。因此,对于这幅画的解释应是困苦中仍然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冬天过去即是春天。
不管如何解释画家作此画时的心情,这幅画的构图、色彩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幅经典之作。画面上横的和直的线条分割、冷的和暖的色彩对比,既合理而又巧妙,显示了画家的功底和机智。
1942年,庞薰琹深入到“ 地无三里平” 的贵州山区,当地土著居民的歌舞和淳朴的性格、健壮的体格、欢快自立的精神,极大地吸引了他。他踏遍八十多个苗家村寨,用他的画笔创作了二十幅《贵州山民图》。《橘红时节》便是其中的一幅。庞薰琹在创作《贵州山民图》时,选择了一种适合表现个性特征的独特艺术形式,那是中西绘画融合成有机整体的崭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标志着他是在与法国的传统决裂中探索着自己的艺术道路,因而有的批评家称这批作品为“ 他的艺术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 。为此,其中10幅为英国皇家协会收藏,其余则为中国美术馆所珍藏。
从《橘红时节》这幅画上可以看出,画家将画面作了高度平面化和装饰化的处理,写实和变形结合起来,具体的人物形象和非具体的装饰图案结合起来,再现客观对象和表达主观情感结合起来,作品艺术形式和谐完美,从形式美的外表迸发出艺术家心灵深处的激情。同这一时期不少效力于融合中西绘画技巧的画家相比较,庞薰琹无疑走在这支队伍的前列。香港的高美庆博士在《20世纪的中国绘画》一书中如此评论庞薰琹的这批作品:“ 线条的运用与赋予图案性造型,使他这类作品具有一种柔和、优美的魅力和极强的装饰性。……庞薰琹是透过中西艺术合壁,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
诚然,面对开发一种不曾有过的新的审美观念的确立,道路是不平坦的。恰如画家在《自剖》(1943年)一文中所述:“ 我所描写的贵州的同胞,无容讳言,与实际的他们离得很远。不能拿民族学的尺寸来量它。因为笔下总不免流露出自己。可是服饰方面,曾尽量保存它原来面目,因此,给我不少束缚,……” 。[庞薰琹认为,这些装饰图案是苗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是表达他们艺术的一个丰富多彩的方面,是苗族人民生活的一个特色。在他的创作中,苗族装饰艺术和苗族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祇有引用和发展到工艺美术中去的时候,它才是孤立存在的。]
背篓
继于四十年代初完成二十幅《贵州山民图》之后,庞薰琹于1946年回到上海,又以同样的手法,以苏南农民为对象,创作了水彩画《背篓》、《小憩》、《捉鱼》、《割稻》等作品。《背篓》是其中最精彩的一幅。
这幅作品,造型的真实和写意结合,形意兼备。
和画贵州苗民的服饰一样,画家刻意细致地描绘了印花布衫的图案,但与苗民图不同的是,这种刻意的描绘也用于背篓的编紮和作为背景的树叶的描绘,因此,少了原先那种生硬拼贴的感觉,从而成为一幅完整的、富有装饰趣味的作品。
同时,于人物神情的刻划,庞薰琹也下了更大的功夫,温柔、内秀的气质和健美、勤劳的外在体形结合,塑造了完美的东方女性形象,尤其是眉宇间含蓄的表情描写,很有些东方蒙娜丽莎的意味,十分耐人咀嚼。
庞薰琹此系列的创作于重庆展出时颇引出一番争议,有人批评他画“ 美人儿” 或“ 唯美主义” ,更有人贬为“ 多少带些低能的趣味主义的东西。” 但庞薰琹在《自剖》中反驳道:“ 十多年前读邓肯的自传,看惠格曼的表演,又曾数次仔细参观印度尼奥太·依奥迦的舞蹈,自那时起在我胸中时时起伏种种幻象。我曾有过这样痴愿,想研究已绝亡的汉族的‘舞’,可惜环境、时间、精神,都不允许我实行我的理想。近年来,我的兴趣又转到古代的图案,连带对于服饰也发生了兴趣,……所以,我用手边有限得很的资料,凭我的想像作此舞装。……现在赶快去研究还来得及找到一点贫乏的参考,不然连一点贫乏的参考,也会被时间消灭了的。为保存中国的文化著想,不见得是无所谓吧!” 现在看来,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民族危亡关头,一些人对艺术家提出苛刻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学者的庞薰琹想的是做学问,不免显出十足的书生气,因此,他的这组作品不免不合时宜。而于半个世纪后再看这些创作,诚如英国美术史论家苏立文于《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一书中所述:“ 他的精神系列画‘舞蹈者’,渊源于他对唐代艺术与服饰的研究,也同样引人入胜。这些作品尽管使用的是中国画笔,在其理想化的加工中,透露出对西方艺术的熟稔。” 确实,从这组作品里,我们感受到了盛唐风范,却也觉察到了那个时代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而在表现技法上还可以隐约觉察日本浮世绘的趣味,而当庞薰琹还在巴黎的时候,欧洲现代画派大师们正对日本浮世绘崇拜得五体投地,苏立文所指的“ 西方艺术的熟稔” 也许指的就是这一点,不少欧洲现代派画家都临摹过浮世绘。
尽管对这组画的舆论褒贬不一,不过庞薰琹却斩钉截铁地声明:“ 似乎因为我画这些唐装,有人就说我画‘美人儿’。这新的‘头衔’,我祇能拒谢。我不单不是唯美主义者,而且我也反对唯美论。这类作品我第一次试作,但也将成为这类作品的最后一次试作。” 不过,1946年,傅雷为他举行第六次个人展览时,非常佩服他的“ 铁线” 钩勒技巧,所以一再希望他能展出这些作品,因此他复制了几幅带彩的。这一幅就是其中之一。1983年,这些作品又一次在纪念他执教五十二周年时于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庞薰琹画展》中展出。
这幅画记录的也是画家于四十年代在四川郫县的旧居,但这是一幅构图和色彩奇巧的佳作。
庞薰琹一再说过:“ ……如果,我的作品能使你感到一点美感,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他确实如此对待他的每幅作品。在平凡中发现美,然而加以表现,把美奉献给人们。
在这幅画的画面上,一片小小的竹林,一幢平常的木屋,经他妙手经营,给人无比温馨。他巧妙地将19根竹枝、8根树杆和10根房柱,用5根椽梁和一排窗户加以分割,应用的仍是他所熟稔的现代构成分割的原理,但那么自然、机巧。无怪乎,有位批评家评述他的作品:有古典主义的和谐、完整、庄重与肃穆;有浪漫主义的诗情;有写实主义的诚实;有表现主义的虚灵;有印象主义的率真;有一切形式主义的智巧。就在这么一幅小小的风景画里,我们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竹林的宁静。画家就在这幢房子里整理着他收集来的许许多多古代纹样,设计着中国工艺美术的未来。这幅画现在由画家的妹妹收藏于上海的家中。
据庞薰琹的女儿、女画家庞涛回忆:“ 父亲不画花。因为妈妈专门画花,他认为他不如妈妈画得好。”
但自前妻丘堤女士去世后,他开始画花,而且画了很多花。画得很有心意。庞薰琹自述:“ 是不是我爱画小油画?不是。因为我的房间里,找不出比两米大的空地。是不是我爱画花?也不是。我想画人,谁敢理睬我让我画?……祇有花,有些好心人採些野花送我,我还在垃圾箱中捡些人家不要的花,我把倒头烂叶的花画得美些……” 这是蒙难的庞薰琹在苦难日子里的辛酸回忆。显而易见的,那时他画花,既是无奈,却也是精神的寄托。
他画花,不是简单的模写对象,而是根据画面需要构图变化,既依据对象,又不完全依据对象,而任凭自己的意图经营画面。他不无意地对人说:“ 有时别人送我一枝很好看的花,我就不断变换这枝花的放置位置,可以画出一簇好看的花来” ,他就是这样在苦难中找“ 乐” ,忘却了自己,把大自然赋予的一丁点美,一丁点生气,放大,升华,再现于画面,既是他高尚、乐观的情操体现,也是他于绘画艺术的奉献。
这幅《美人蕉》是他这一类花卉作品的一个典型。不难看出,整个画面(包括背景)是画家“ 设计” 的结果,花、叶陈列有致,色彩对比靓丽,富有强烈的装饰趣味。
一大把盛开的花朵插在一只宋瓷花瓶里,形式和谐完美的画面充满了装饰的美。整个画面作高调处理,色彩鲜明,构图饱满,显示出蓬蓬勃勃的生命力量。很难想像这样一幅充满生命活力的作品,却是一位不久前刚从“ 牛棚” 里放出来,还背着沉重的政治冤屈未获平反的老艺术家的手笔。
王安石曾有这样的诗句:“ 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何缘身处逆境的庞薰琹却能用自己的画笔把春色凝固于画面而永驻人间?他的一首题为《小草》的自喻诗,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注释:“ 一颗平平常常的小草,虽然饱经烈日秋风、旱涝雨雪,毕竟不可摧折,春风吹又生,始终顽强如故;甚至即使连地下的老根也枯死了,可是在死去的老根旁,却又长出新根长出了新芽,草地仍是一片绿色……”
永远乐观的信心,永不疲倦的探索,使老人永葆艺术的青春!他从不使自己笔下的花带有伤感,不论是浓彩艳丽的鸡冠花,还是淡雅飘逸的水仙花,都给人以具有生命力的美感。
诚然,庞薰琹的画花,除了寄情、言志之外,更热衷于艺术的探索。从这幅画里,我们看到画家感兴趣的不仅是关于装饰性的设计意匠,更对色彩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
他在这幅画中,可以说把对象的固有色的色相强调到极顶,全然不顾所谓环境色的制约。他认为:“ 色彩有巨大的作用” 。“ 一切器物如不加上点色彩,那么生活一定变得枯燥。” 过去士大夫阶级认为浓色不如淡色雅,淡色不如墨色高。几百年来受著这种理论的影响,使美术工作者在色彩的表现力上比较弱,在色彩的感觉上也比较迟钝。“ 不重视色彩的研究,这是非常错误的。” 他力图通过器物固有色的描绘,来提高画家对色彩的敏感和表现力。他在这幅画中,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人们:对比的固有色,可以在同一画面上取得和谐的美。而他对白色瓷瓶在高调画面上的描绘,更显示了他表现固有色的高超本领。
庞薰琹好象很喜欢画鸡冠花,在他的作品中有好几张鸡冠花,情趣各异。有的绘画性强,有的装饰性强,有的严谨、有的洒脱。这张作于1984年的作品,把鸡冠花和吊兰画在一起,用笔轻松活泼,色彩浓艳强烈,充满活力,很难令人相信出自一位七十七岁老翁之手,这也许和他政治上得到平反、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庞薰琹的梦又获得重新编织的机会,心境愉快有关。但人们没有预料到他两年后就匆匆离开了人间,因此,有柆美术评论家认为:如果庞薰琹能继续活下去,他在绘画方面将恢复年轻时代的活力,作为曾是三十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领头人,他必将在八十年代的青年美术新潮运动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使青年美术家少走不少弯路。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笔者认为庞薰琹如果活着,未必会和“ 85新潮美术” 的那些青年走在一起,正如与他同时代的洪毅然在纪念庞薰琹的文章《探索者的足迹》一文所述:“ 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实乃远远不自今日始。不过,我们那时的‘现代’概念,其内涵却与当今某些误解‘现代化’即全盘‘西方化’的人们之‘现代’概念,并不相同。我们虽然也不排除适当吸收西方艺术(包括其‘现代派’艺术)某些于我可用之形式和技法,却仍始终坚持贯彻‘中国学术现代化,外国学术中国化’之原则,既不顽固保守,复古倒退,也不亦步亦趋紧跟洋人爬行。” 老一辈的道路早已经过自己的实验而选定,而青年人是一定要亲自把西方现代绘画一百年走过的路再走一遍才会认定自己该走的路,尤其是因为大陆与外部世界封闭了四十年,庞薰琹又经过如此坎坷,青年人未必会听从他的劝导。有趣的是,洪毅然在同文中记述了庞薰琹二十年代初到巴黎,也曾于夜间,把两眼闭起来涂抹,借求意外的‘现代’效果。而当今一些青年人还把寻求‘潜意识’的灵感,当成时髦的新玩意!
未圆的梦
有人把庞薰琹称为“ 中国前卫艺术之父” ,因为在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程产生历史性影响的三位同时代画家中,他既区别于徐悲鸿立足本土、选择写实绘画来超越中国传统绘画的价值体系,又不同于林风眠以中西艺术的调和来确立新的艺术价值体系,而是中国画家中,最早入流西方现代艺术潮流,把价值取向定位于前卫艺术而回归本土的一位先驱画家。可惜的是,这位本可以成为中国第一位前卫艺术大师的天才画家,他的才华却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中被扼制,从四十年代开始就转而从事工艺美术,留下了一个未圆的“ 薰琹的梦” 。
薰琹的梦
著名翻译家和美术批评家傅雷于民国二十一年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的开幕,曾于《艺术旬刊》发表一篇题为《薰琹的梦》的文章来分析庞薰琹的创作之路。文章说:“ 他从童年时无猜的梦,转到科学的梦非所梦,音乐的梦其所梦,至此,即开始创造他的《薰琹的梦》。” 庞薰琹的“ 梦” 是怎样编织起来的呢?除了震旦大学那位外国神父说“ 中国是出不了大画家” 的刺激外,当时中国画坛的衰微更促使庞薰琹要成为一位改变中国现代美术面貌的斗士。当他到了巴黎“ 一切新的,旧的,醜的,美的,看的,听的,古文化的遗迹,新文明的气焰,自普恩克尔(Poincare)至Josephine Baker都在他脑中旋风似的打转、打转。他,黑丝绒的上衣,帽子斜在半边,双手藏在裤袋里,一天到晚的,迷迷糊糊,在这世界最大的漩涡中梦著……。” (傅雷:《薰琹的梦》)终于他作出了选择,放弃了进“ 学院派” 统治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的机会,而进了位于巴黎艺术活动中心蒙巴拉斯(Montparnasse)的格朗歇米欧尔研究所(La Grand Chaumiere)学习,因为在那里他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新派艺术家如“ 巴黎画派” 中毕卡索、凡童根(Van Dongen)、古斯林、尤特里罗(Utrillo)、雕塑家布尔德尔(Bourdelle)等人和其他新潮文学家、舞蹈家、艺评家的谈艺说文,学到许多从学院里学不到的东西,不仅窥见了许多人盛名背后的虚华,也感受到了一些现代画派画家的质朴的淳厚,他尤其崇拜毕卡索的勇气、才华和气魄。
无疑,参观十二年一遇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也给他的梦凭添一份创造的色彩。他感到建筑风格和装饰艺术风格正在影响着时代风格的变化,由此改变了他纯绘画艺术的观念。民国十七年(1928),他还到德国考察了受包豪斯影响的建筑和艺术,接受了融建筑、雕塑、绘画为一体的包豪斯思想。这对他日后创作中的装饰风格和工艺美术设计,起了一辈子的影响。当他看到一个高水平的日本画展在巴黎的轰动之后,又受到古堡咖啡馆那位权威批评家的指点,他深信“ 从哪种土壤里出来的芽,也祇能在同样的土壤里生长、开花、结果。” (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于是带着西方前卫艺术意识,决心回归本土演绎他的“ 薰琹的梦” 。
决澜社时期
回到祖国,他“ 梦一般观察” ,“ 梦一般寻思” ,“ 梦一般表现” ,“ 他把色彩作纬,线条作经,整个人生作材料,织成他花色繁多的梦。他观察、体验、分析如数学家,他又组织、归纳、综合如哲学家。他分析了综合,综合了又分析,演进不已;” “ 他变形,因为要使‘形’有特种表白,这是Defornisme espressive。他要给予事物以某种风格,因为他的特种心境(Etada’me)需要特种典形来具体化。” “ 他以纯物质的形和色,表现纯幻想的精神境界;” “ 然而在超现实的梦中,就有现实的憧憬,就有时代的反映。” “ 我们一般自命清醒的人,倒不如站在现实以外的梦中人,更能识得现实。” 傅雷对《薰琹的梦》的剖析,概括了庞薰琹三十年代“ 决澜社时期” 全部创作的艺术特点和艺术价值,十分精辟。在决澜社时期,庞薰琹不仅是中国早期现代艺术运动的组织者,更是推进中国早期现代艺术骁勇的主将,短短几十年中,他推出众多作品,展示了中国早期现代艺术的形式与精神。如果说他的《西班牙舞》、《藤椅》、《女裸》、《屋顶》等作品还存留着西方现代流派的余韵,《在画室中》、《丘堤像》等作品以现代美术形式构成融入东方情韵的装饰绘画语言,那么,他的《地之子》、《无题》、《人生哑謎》、《如此上海》、《如此巴黎》和《路》,则借鉴了西方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的表现形式和艺术精神,把他回国后亲身感受到的社会现实和他忧国忧民的思绪,通过超时空的现代形式构成尽收进他的画面。誠如陶咏白《对庞薰琹的历史思考》一文所指出:“ 他的作品与同一时代的徐悲鸿用写实手法画的《田横五百士》、与林风眠用表现主义手法画的《人道》、《痛苦》等主题画相比较,具有异曲同工的社会功效。” “ 庞薰琹的作品较之徐悲鸿用历史故事来影射现实更贴近生活。他与林风眠一样是重主观表现型的画家……。林风眠注重情感抒发中赋予画面大的运动节奏的美感……使画面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庞薰琹则在理性的组织画面中追求着装饰美感,并赋予其更深广的内涵而发人深思。”
无疑,庞薰琹于“ 决澜社” 时期的创作,是他艺术道路上最光彩的一页,它突破了中国美术的审美传统,点燃了时代审美精神的火花。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星火花未能成炬,但过了半世纪以后,这一星火花仍然激励起中国的青年美术家们举起火炬,大步迈向庞薰琹所选择的价值目标!
梦的转折
决澜社的被迫解散,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流亡生活,使庞薰琹的艺术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诚如他的《自剖》所述:“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渺小的我在这个时期,一步紧一步地感到惶恐,我虽想全身投入东西方文化的怀抱,不过我太渺小了。也许,我祇能像流沙一般,被洪流吞没……。” 他中断了具有时代博大宏伟精神和深刻内涵的前卫绘画艺术的探索,他忍受不了前卫艺术在中国这块特殊的文化土地上的孤独,同时又深感于此民族危亡的时代,艺术不是表现“ 自我” 和强调“ 个性” 的宠儿,“ 现在我以为写黑暗不如写光明;人生需要艺术,艺术能给人以鼓励……这伟大的时代使我渐渐忘了小我,也许我能步入另一个境界……。” (《自剖》)他深入到“ 地无三里平” 的贵州山区苗寨用毛笔画了一幅幅《苗家女》,完成了20幅《贵州山民图》和一批唐装舞女图。这些画,他作了高度平面化和装饰化的处理,写实和变形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虽不如决澜社时期作品那样洒脱、奔放,但在艺术形式上比较和谐完美,在掌握传统绘画技巧线描方面,趋向老到成熟。然而这些作品又流露出了画家在艺术思想转变过程中进行探索的种种苦恼。“ 我爱沉思,我爱冷静的头脑……我爱毕卡索,于是,我爱火热的心。甚而至于我爱炸弹。我当然不是爱他的残忍,我爱他的外表又笨又冷,在这笨和冷的外衣中裹着火热的心。这种种爱好,就是组织成我画面的源泉。” 但是,显然他在这样的探索中感到“ 苦闷而又低能!(引文均自《自剖》)整个四十年代,他就处于这种转折斯的探索中,《背篓》、《橘红时节》、《情话》、《笙舞》等作品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来不及重圆的梦迹
四十年代的开始,庞薰琹就为实现另一个梦,即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的、现代的工艺美术学校而注入他越来越多的心血,这一努力明显地反映于他的绘画创作里,在一幅幅反映苗民生活的作品中,他详实的记录了苗民的服饰图案,甚至于不顾由此而使画面产生拼贴感。进了五十年代,他几乎停止了创作,全身心地投入创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及其教学理论体系的工作,并于1956年实现了这个梦,却又于翌年反右运动中砸碎了这个梦。当他二十年后又有机会重圆这个梦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遭到十年政治动乱破坏后的中央工艺美院,尽管他以七十高龄的耆耄之躯加倍奋力工作,然而,时间已经不夠了,他匆匆离开了人世。绘画本来就是庞薰琹的生命之源,它神奇地使庞薰琹摆脱了疾病和苦恼,又重新生活在自己构筑起来的诗意中。他在鳏居多年后又结了婚,有了女儿。如他平反后写的一首诗所述:“ 二十二年这样长的时间会留下一些痕迹/在我身上是一头白发/满身疾病/可是在我胸膛中/有一颗火热的心/它在跳/现在跳得那么激动/它又跳得那样平稳/过去就让它过去吧/现在还是向前看吧!” 他在编写《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一书的同时,不停地用油画在室内画花,百合花、美人蕉、鸡冠花、白菊花、牵牛花……朋友们给他一枝花,他得意地画成一簇花,他把悲哀留在心底,把美好留给人间,他把自己无私、乐观的人格情操倾注于他的花的系列作品中,每一幅《花》,无不流露出清新、平和的意蕴,表达了画家淡泊明志的情趣。综观庞薰琹于蒙难时期和政治上获得平反以后的一系列花和风景的创作,虽然已不见他青年时期作品那种用笔大刀阔斧,具有深刻内涵和冲击力的作风,但仍见他不疲倦地运用现代现式规律,力求在平凡的画面上求得审美观念的突破,色彩和肌理的处理非常精美,集装饰性和绘画性为一体,有许多作品的色彩、构图、肌理、形式处理,堪称经典。评论家认为:如果这些作品不是在身处逆境或平反后“ 心有余悸” 的情况下产生,一定会更少拘泥;而他如果能多活二十年,必将重新成为中国一代前卫艺术的巨匠。可惜的是:生不逢时!薰琹的梦是个未圆的梦。
庞薰琹作品解读
庞薰琹早在巴黎时就对工艺美术的图案设计感兴趣。回国后,收集了上千幅中国古代青铜、陶瓷、丝绸和漆器上的纹样,并于此基础上在四川郫县创作了一本《工艺美术设计》,1944年交友人带到国外出版,辗转三十余年后,由英国美术史论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带回北京交还庞薰琹,198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四幅方盒图案设计是1939年在昆明创作的《中国图案集》100种设计中的四种,也是以古代纹样变形手法设计,曾在昆明展览,获学术界高度评价。
庞薰琹1940年设计的《工艺美术集》将中国古代纹样与现代设计意识相结合,创造性的开辟了一条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设计道路,至今影响深远。这批设计作品,在阔别了三十余年之后,由好友牛津大学教授苏立文从英国带回北京。但遭阻无法见面,数次之后才得机会,完璧归赵,亲自交到庞薰琹手中。原作崭新如初。时隔不多日,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将其出版,然而这批珍藏的精品,竟然被直接送到工厂制版,一本小小的工艺美术设计出版之后,原作被污损到了不堪入目之地步,庞薰琹再次见到自己这批作品时,亦奈何不得。(庞均撰文)
晚年的庞薰琹进敦煌、下江南、去山东考察和讲学,一路画了不少小幅写意风景,别具一格,用笔简练洒脱,颇有韵味。(周昭坎撰文)
青年时代的庞薰琹激烈地反对刻板机械地模仿“ 自然主义” 和所谓“ 写实派” 的绘画。他认为这种模仿自然的绘画,在现代“ 以数秒钟的时间拍一张照相,不会较描写数个月的一幅少真实。” 由此,他主张艺术家应该利用各自的技巧,自由地、自然地表现事物和自我。他的艺术主张,在《决澜社宣言》中更表白得十分明确:“ 我们厌恶一切旧的形式,旧的色彩,厌恶一切平凡的低级的技巧。我们要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时代的精神。……野兽派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 达达派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二十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出现一种新兴的气象了。”
1932年前后创作的《如此巴黎》、《如此上海》、《人生的哑謎》、《画室内》和1938年创作的《路》,有别于同时期创作的《地之子》、《三个女性》那种沉静的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力图用激烈的绘画语言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绪。用庞薰琹自己的说法是“ 我的一生,是探索探索再探索的一生。” 他一直在尝试用各种手法表现不同的主题。
在《如此巴黎》这幅作品中,画家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形象,用“ 蒙太奇” 手法剪辑,以现代构成方法处理构图,将繁华而疯狂的夜巴黎浓缩在一个画面上,卖笑的女人、赤裸的身体、愁苦的眼神、叼雪茄的男人、隐现的警察、摇曳的灯光、眩目的广告,便是一扇门、两扇窗和几张纸牌,也在时刻变幻着。
《如此上海》、《人生的哑謎》采取了相同的手法,表现了类似的内容,可以认为是画家于这一时期思考社会现象的一组系列画。这组作品的表现手法虽然未脱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影响,但是,在形象、色彩方面具有装饰性,显然较为接近东方人的审美情趣,错综复杂的组合却不失谐和自然,激烈变幻的表现却不失平衡合理。
《人生的哑謎》傅雷说庞薰琹以艺术家无猜(Innocent)的童心,再现了人生的梦,是明白地悟透了之后造出的清醒的假梦,是从现实中提炼出若干形而上的要素,在探求人生之哑謎。所以虚幻的画面反映的是真实的人生,表达的是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周昭坎撰文)
这幅油画作于巴黎,画得很轻松,颜色调得很稀薄,画面也没有塗满,有的地方如衣褶,如画中国画一般,一鉤了之。他认为油画的画法不应有定规,严谨的古典画法或塗鸦式的信笔作画,如同书法的蝇头小楷与狂草,各有千秋。(周昭坎文)
(另附庞均《自画像》1993年,65*53公分)庞氏一门为浑然天成的艺术之家。庞薰琹与其子庞均皆为天才型的创作者,但因时代的变动,使得庞薰琹的创作生涯历经几多波折。庞薰琹此画作于其逝世前两年,其眉宇间内斂而历尽沧桑,仿佛是抒发时不我予的嗟叹。(林妙玉撰文)
庞薰琹在年轻时代,尝试了西方绘画各种流派的画法,最后选择了从西方回归东方的艺术道路。他在尝试各种新画法时,并不是简单地模仿抄袭,而是溶入了他自己对描绘对象和适合这一对象的表现方法的理解,所以,他的用笔自然、流畅、没有造作的痕迹。这幅《籐椅人体》是他最得意的一幅早期作品。虽然是一幅学习马蒂斯风格的习作,但其神韵不失大师风范、简炼到多一笔即为添足的线条、洒脱流畅;夸张的变形也是到了极致,头部的大小尽管和腿的比例失调,但是,再大一点或者再小一点,这幅画就没有美学价值;籐椅的黄色和人体的肉色非常接近,同样也是调色板上多一分别的颜色配比,就会失去这种和谐的对比。这幅画过去很少有机会与读者见面。因此特地介绍。可惜原作已不复存在。据画家的女儿庞涛(也是一位著名女画家)回忆,抗日战争爆发时,从北平带出的一卷二、三十年代的作品,总共有20多幅,这一幅也在其中,而现在祇剩下了《法国老人像》一幅。
安玛瑞儿(Tarsila do Amaral ),"Abaporu",1928年,油画。在二十世纪初,一群来自拉丁美洲的艺术家蜂涌至巴黎习画。如同庞薰琹一般,这些艺术家身处于西方美学观念主导的冲击后,经过一番审思之余,最后泰半在追溯根源及对自身文化认同的过程里落叶归根。巴西女画家安玛瑞儿即是一例。此画融合了当时主流画派的立体主义与超现实派别的表达意识,以简单而夸张的造型,表达出对其特有文化的孺慕与崇敬。于此所有欲被阐述的对象,其造型都被约简到最单纯的地步,没有一丝丝多余累赘的线条来干扰构图所欲传达的讯息。图中主体休息于地面,象征着与土地之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其粗硕的四肢和细小得不成比例的头部及模糊的五官,与庞薰琹的《滕椅人体》颇有相似之感。(林妙玉文)
这是庞薰琹有感于当年江南大旱,土地龟裂,民不聊生而花了几个月时间创作的一幅作品,本是一幅油画,曾于1932年他在上海举行的首次个人展览及在第三次决澜社作品展览中展出,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展出时曾轰动一时,但后来被当局认为有“ 赤化宣传” 嫌疑,受到攻击,他本人收到匿名恐吓信,不久,法租界巡捕还准备缉捕他,他在傅雷的帮助下逃到了杭州躲避。据说这幅画后来由四川博物馆收藏,但又转手一家外国博物馆买去。现在这幅是1934年用水彩画复制的,油画原作已散失(编者注:水彩画原作现藏庞薰琹美术馆)。
画面上是一个将死的僵硬孩子,横卧在一个农民模样的男人手中,这个男人一手扶着孩子,一手握拳;孩子的母亲俯首靠在丈夫的肩上,掩面而泣。他们穿戴整齐,看上去体质健康。据画家自述,他是用这对健美的青年夫妇来象征中国,而用将死未死的孩子隐喻当时的中国人民。
无疑,画家是充满感情完成这幅油画的。据说,他回到常熟家乡,亲眼看见农民把地契贴到地主的大门上,便全家离乡背井逃荒而去,庞薰琹含着同情的泪水创作了这幅画,他试图采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来创造一幅主题是中国总有一天会摆脱贫困的作品。
我们注意到画家创作的是一种被压抑而又平静的人物情感。他采用简化和拉长了的形体描绘,大面积平涂,以平面、装饰的风格来表现朴实和力量,十分成功。这种风格不由使人联想到毕卡索蓝色时期的作风。画家承认他最佩服的就是毕卡索。但他决不是模仿和照搬。他主张“ 中国学术现代化,外国学术中国化” ,他吸收外来形式,却注入了中国人的情感、神韵,包括造型和线条的运用。可惜像《地之子》这样具有时代博大宏伟精神和深刻内涵、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作品并不多见。
这幅与《地之子》同一时期、同一风格的作品,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生活于苦难中而憧憬着美好未来的中国女性,同样是一重既压抑而又平静的人物感情,因此,当时有人认为他的作品只暴露了社会的黑暗,没有指出光明的希望和对黑暗的反抗。庞薰琹承认这段时期的作品蒙上了“ 一层薄薄的哀伤” 。但是,他说他爱炸弹那种“ 笨与冷的外衣中裹着火热的心” ,因此,那种压抑而沉静的表情,何尝不是一颗会发出光和热量来的“ 炸弹” 呢?庞薰琹经常说他的作品是“ 文学的绘画” ,因此,许多深邃的含涵,不像德国表现主义绘画那样鲜明、强烈,而是需要花时间细细地去“ 读” 和体会的。整个画面使用的绿色色调,即是画家用于暗示生命的活力,和那画面上三位清秀的女性形象所想表现的意念是一致的。(周昭坎撰文)
在庞薰琹的作品中,有几幅以他生活历程中关系重大的几处住处景象为题材所作的风景画,是反映画家真实心情的精心佳作。这幅《白家庄旧居雪景》,有人认为是画家政治上蒙冤后所作的第一幅作品,阴冷、 滞凝、沉重的情调,反映了他被免职后打发到东郊白家庄两间斗室离群鳏居的忧愤、委屈、迷惘的心情。
其实仔细分析这幅画面的情调并非如此。厚重白雪覆盖的新兴城郊,虽然冷清,但一片微弱温暖的阳光映照着新建的住宅,如同同一时期画家在白家庄斗室里画的那些花卉,透露出的是一样的乐观和富有生机。庞薰琹本是一个乐观豁达的艺术家。当他刚搬到白家庄时,固然因为蒙冤、妻子丘堤去世,使他一月间黑发全白,病至垂危。但经一位老中医点化,知医药无效,全靠自我解愁,于是拿起搁置画笔开始画花,心情逐渐开朗,病渐痊癒。1963年,他又与袁韵宜女士结婚,领一女,生活重新有了信心。因此,他那时虽因作为“ 摘帽右派” ,担任教学工作中仍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发生,但心情上总还是乐观的。因此,对于这幅画的解释应是困苦中仍然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冬天过去即是春天。
不管如何解释画家作此画时的心情,这幅画的构图、色彩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幅经典之作。画面上横的和直的线条分割、冷的和暖的色彩对比,既合理而又巧妙,显示了画家的功底和机智。
抗战胜利后,庞薰琹全家自四川返回上海,居住在英租界虹口区,狄思威路,一座三层的楼房。他整日在阁楼中埋头作画。大批唐代白描舞蹈图是在此完成的。这幅油画风景,表现了典型的欧式楼房与前景的中式瓦房,形成有趣的对比,整幅作品淡雅平和,清新隽秀。(庞均文)
这幅画原是一幅水彩,作于四十年代,现由当时的邻居傅雷之子,著名音乐家傅聪保存。1973年,画家按水彩原样复制了这幅画。画家于四十年代在牯岭旧居度过了战争时期动荡而有意义的时光。他在那里深刻地了解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完成了从外国艺术传统中摆脱出来的挣扎,走上了回归和发展民族传统的艺术道路,并为发展中国的工艺美术教学作了有益的铺垫。而与邻居、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亲密相处的友情,更使他难于忘怀,特别是傅雷夫妇于“ 文革” 中的自杀,更使遭到相近劫难,刚从“ 牛棚” 里放出来的庞薰琹勾起了往日的回忆和对挚友的悼念。(周昭坎撰文)
纯写风景的画作在庞薰琹的作品当中,虽然不是占有很重要的比例,但是对画家来说,皆赋有生命中另一层写实的意义。本幅这种以俯瞰的视点来安排场景的饰局,通称为全景画(Panorama)。这样的视点处理,常使透视的层面不仅由近到远,空间亦随之向垂直高低的方向逐渐扩展。仿佛登高峰而望之,视野辽阔,一景一物皆尽收眼底。(林妙玉文)
1938年,庞薰琹深入到“ 地无三里平” 的贵州山区,当地土著居民的歌舞和淳朴的性格、健壮的体格、欢快自立的精神,极大地吸引了他。他踏遍八十多个苗家村寨,用他的画笔创作了二十幅《贵州山民图》。《橘红时节》便是其中的一幅。庞薰琹在创作《贵州山民图》时,选择了一种适合表现个性特征的独特艺术形式,那是中西绘画融合成有机整体的崭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标志着他是在与法国的传统决裂中探索着自己的艺术道路,因而有的批评家称这批作品为“ 他的艺术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 。为此,其中10幅为英国皇家协会收藏,其余则为中国美术馆所珍藏。
从《橘红时节》这幅画上可以看出,画家将画面作了高度平面化和装饰化的处理,写实和变形结合起来,具体的人物形象和非具体的装饰图案结合起来,再现客观对象和表达主观情感结合起来,作品艺术形式和谐完美,从形式美的外表迸发出艺术家心灵深处的激情。同这一时期不少效力于融合中西绘画技巧的画家相比较,庞薰琹无疑走在这支队伍的前列。香港的高美庆博士在《20世纪的中国绘画》一书中如此评论庞薰琹的这批作品:“ 线条的运用与赋予图案性造型,使他这类作品具有一种柔和、优美的魅力和极强的装饰性。……庞薰琹是透过中西艺术合壁,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
诚然,面对开发一种不曾有过的新的审美观念的确立,道路是不平坦的。恰如画家在《自剖》(1943年)一文中所述:“ 我所描写的贵州的同胞,无容讳言,与实际的他们离得很远。不能拿民族学的尺寸来量它。因为笔下总不免流露出自己。可是服饰方面,曾尽量保存它原来面目,因此,给我不少束缚,……” 。
庞薰琹认为,这些装饰图案是苗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是表达他们艺术的一个丰富多彩的方面,是苗族人民生活的一个特色。在他的创作中,苗族装饰艺术和苗族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祇有引用和发展到工艺美术中去的时候,它才是孤立存在的。《盛装》局部,1942年,水彩画,43.5*35公分,中国美术馆藏。不难看出画家对民间图案怀有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贵州山民图》系列画,确实是珍贵的苗族风习与服装的研究资料。《情话》,1943年,水彩,46*19公分,庞薰琹家属藏。在完成《贵州山民图》的同时,庞薰琹还画了一批反映苗民民俗的作品。
《持鎌》,1942年,白描,42*32公分,中国美术馆藏。《归来》,1944年,白描,42*32公分,中国美术馆藏。《走亲》,1943年,白描,42*32公分,庞薰琹美术馆藏。《母与子》,1944年,白描,42*32公分,中国美术馆藏。这些白描作品是庞薰琹的创作素材,而有一些显然又于事后重新画过,本身即似中国古代《绣像》类的创作,四十年代的庞薰琹是白描高手,眼明手巧,走笔如行蛇,游丝似银钩,傅雷称赞他“ 具有东方人特有的气质,他的线条艺术成就很高,是东方人中的佼佼者” 。(周昭坎撰文)
在庞薰琹的作品里,静物的作品(不包括花卉)并不多见。这幅于四十一岁时作于广州的《静物》,构图、造型和色彩都很严谨。
对于庞薰琹来说,“ 严谨” 的含义决不是毕恭毕敬地自然主义地描绘对象。一如他的一贯作风,他在描绘对象时,写实和写意、绘画性和装饰性巧妙地揉和在一起,而在这一幅作品中,更让人觉得“ 天衣无缝” 。
譬如画面上的石膏头像和梨是写实的,而陶罐的背景上的壁毯都是装饰性的画法,二者既是对比的,又是谐和的,显然深沉而丰富的色彩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而所有的色彩又突出了梨的黄嫩,使整个画面产生亮暗轻重多层次的效果,情趣横生。
庞薰琹一直热衷于图案画。他借用这幅静物“ 写生” ,在壁毯和陶罐上尽情地表达了他对图案的热情,刻划得十分仔细认真。这也许与他当时正在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开设工艺美术课不无关系,他希望学生在学习绘画基础课程的时候,就开始对图案设计产生兴趣。因此,这幅作品极可能是当时的示范作品。
无所不在的装饰情趣
庞薰琹在1957年于“ 反右” 的声浪中,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有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几乎停止艺术的创作,而这段真空期也使他与早期前卫的艺术之路造成断层。其后的有生之年只专注于小幅花卉的描写,而不论艺术界的风云。尽管如此,此间他在装饰画方面投注精力,费时二十年始编纂而成的《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对中国文化仍是一项不可抹灭的贡献。本专栏所摘选的画作局部,即可显示出庞氏在创作上对装饰绘画的一贯性。其实在早期之同质性的淡彩与线描勾勒的画作中,如《盛装》及《带舞》系列,无不洋溢着装饰情调。颜色轻俏活泼,线条细緻柔美,有融合装饰与绘画为一体的意图。其装饰意味和创作结合中国传统特殊的人文之美,展现的不仅是艺术创造的功力,亦附有设计上实用的价值。(林妙玉撰文)
1931年庞薰琹与志同道合的朋友酝酿成立“ 决澜社” ;1932年9月中旬庞薰琹在上海开他个人的第一次画展,在此次画展中认识丘堤,而丘堤也因为庞的关系,加入了决澜社,成为决澜社当时唯一的女会员,后来又有女会员加入。1932年10月中旬,丘堤以一幅花卉作品参加决澜社第一次画展,并且得奖。此幅《静物》是第二次参加决澜社画展的作品。庞薰琹与丘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相知相惜而结成连理。(庞均撰文)
《背篓》,1946年,水彩画,46*30公分,中国美术馆藏。
继于四十年代初完成二十幅《贵州山民图》之后,庞薰琹于1946年回到上海,又以同样的手法,以苏南农民为对象,创作了水彩画《背篓》、《小憩》、《捉鱼》、《割稻》等作品。《背篓》是其中最精彩的一幅。
这幅作品,造型的真实和写意结合,形意兼备。
和画贵州苗民的服饰一样,画家刻意细致地描绘了印花布衫的图案,但与苗民图不同的是,这种刻意的描绘也用于背篓的编紮和作为背景的树叶的描绘,因此,少了原先那种生硬拼贴的感觉,从而成为一幅完整的、富有装饰趣味的作品。
同时,于人物神情的刻划,庞薰琹也下了更大的功夫,温柔、内秀的气质和健美、勤劳的外在体形结合,塑造了完美的东方女性形象,尤其是眉宇间含蓄的表情描写,很有些东方蒙娜丽莎的意味,十分耐人咀嚼。
如果达文西通过蒙娜丽莎永恒的微笑的描写,以预示人文主义精神的胜利,那么,庞薰琹显然企图以一位劳动妇女脸上同样表情的描写,召唤着新时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到来。当时,有的批评家批评他不顾社会黑暗面而片面描写光明,导人盲目乐观。庞薰琹即予反驳:“ 我为什么不常写社会的阴暗面,因为现在我以为写黑暗不如写光明;人生需要艺术,艺术能给人以鼓励……反之,过去我的作品时时蒙上一层薄薄的悲哀。” 显然,这是他经过人生体验后选择的创作道路。(周昭坎撰文)
庞薰琹曾哀叹他在蒙难期间想画人而没有人敢让他画。但是,1962年,他的学生罗真如(现在也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主动为他做模特儿。这是他许多年没画人像以后画的第一张人像。这张人像的画法和他十六年前画的《背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幅画后来又由画家复制了一幅送给罗真如。和他创作苗民图时一样,他像“ 绣花” 一般把蓝花布的纹样照原样画出。由于画面上其他道具作了同样精细的处理,整个画面大为统一和谐,别具一种装饰意味的情趣。(周昭坎撰文)
多明尼克·吉尔兰戴欧(Domenico Ghirlandaio)《女人像》,1488年,蛋彩。此幅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不论在姿势的调动以及人物神情的刻划上,都出现了极其相似的安排,而其衣饰的雕琢讲究,也是非常细緻的工笔手法。此种採人物侧身的构图方式,避开对象与观者直接视觉接触所产生的不安,而使画中人与观者双方都较能以第三者的立场参与整个画面所蔓延的氛围。(林妙玉撰文)。
庞薰琹此系列的创作于重庆展出时颇引出一番争议,有人批评他画“ 美人儿” 或“ 唯美主义” ,更有人贬为“ 多少带些低能的趣味主义的东西。” 但庞薰琹在《自剖》中反驳道:“ 十多年前读邓肯的自传,看惠格曼的表演,又曾数次仔细参观印度尼奥太·依奥迦的舞蹈,自那时起在我胸中时时起伏种种幻象。我曾有过这样痴愿,想研究已绝亡的汉族的‘舞’,可惜环境、时间、精神,都不允许我实行我的理想。近年来,我的兴趣又转到古代的图案,连带对于服饰也发生了兴趣,……所以,我用手边有限得很的资料,凭我的想像作此舞装。……现在赶快去研究还来得及找到一点贫乏的参考,不然连一点贫乏的参考,也会被时间消灭了的。为保存中国的文化著想,不见得是无所谓吧!” 现在看来,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民族危亡关头,一些人对艺术家提出苛刻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学者的庞薰琹想的是做学问,不免显出十足的书生气,因此,他的这组作品不免不合时宜。而于半个世纪后再看这些创作,诚如英国美术史论家苏立文于《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一书中所述:“ 他的精神系列画‘舞蹈者’,渊源于他对唐代艺术与服饰的研究,也同样引人入胜。这些作品尽管使用的是中国画笔,在其理想化的加工中,透露出对西方艺术的熟稔。” 确实,从这组作品里,我们感受到了盛唐风范,却也觉察到了那个时代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而在表现技法上还可以隐约觉察日本浮世绘的趣味,而当庞薰琹还在巴黎的时候,欧洲现代画派大师们正对日本浮世绘崇拜得五体投地,苏立文所指的“ 西方艺术的熟稔” 也许指的就是这一点,不少欧洲现代派画家都临摹过浮世绘。
尽管对这组画的舆论褒贬不一,不过庞薰琹却斩钉截铁地声明:“ 似乎因为我画这些唐装,有人就说我画‘美人儿’。这新的‘头衔’,我祇能拒谢。我不单不是唯美主义者,而且我也反对唯美论。这类作品我第一次试作,但也将成为这类作品的最后一次试作。” 不过,1946年,傅雷为他举行第六次个人展览时,非常佩服他的“ 铁线” 钩勒技巧,所以一再希望他能展出这些作品,因此他复制了几幅带彩的。这一幅就是其中之一。1983年,这些作品又一次在纪念他执教五十二周年时于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庞薰琹画展》中展出。
这铁线白描确实是第一流的。庞薰琹的经验之谈是:画白描不能允许一点干扰。情绪不稳定不要画。一开始画应该画到完成,中间吃饭或休息一会也不行。墨水要足那画一幅的,中间加水不行。画人脸从右眼靠鼻梁处动笔,用笔要轻秀,中间隆起。靠眼珠处,用笔手底要加力,这种眼睛可以加深强度。收笔要轻,不留笔痕。更难的是画左眼,从右到左是反手。画了双眼,接着画双眉、鼻、嘴,最难的是人脸轮廓,从额际一直画到头部,一笔画成,用笔要稳又有变化。以上五幅白描作品为庞薰琹的带舞系列,分别是《带舞》之一、之三、之四、之八及之十二。于1942年 ̄1945年间作于成都。尺寸一律33*44公分,为中国美术馆所收藏。(周昭坎撰文)
这幅画记录的也是画家于四十年代在四川郫县的旧居,但这是一幅构图和色彩奇巧的佳作。
庞薰琹一再说过:“ ……如果,我的作品能使你感到一点美感,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他确实如此对待他的每幅作品。在平凡中发现美,然而加以表现,把美奉献给人们。
在这幅画的画面上,一片小小的竹林,一幢平常的木屋,经他妙手经营,给人无比温馨。他巧妙地将21根竹枝、10根树杆和10根房柱,用5根椽梁和一排窗户加以分割,应用的仍然是他所熟稔的现代构成分割的原理,但那么自然、机巧。无怪乎,有位批评家评述他的作品:有古典主义的和谐、完整、庄重与肃穆;有浪漫主义的诗情;有写实主义的诚实;有表现主义的虚灵;有印象主义的率真;有一切形式主义的智巧。就在这么一幅小小的风景画里,我们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竹林的宁静。画家就在这幢房子里整理着他收集来的许许多多古代纹样,设计着中国工艺美术的未来。这幅画现在由画家的亲属收藏于上海的家中。
庞薰琹一生不断改变自己的画风,他觉得用一种画法老画一种题材是最没有意思的。因此,他在灌县写生时画的一组风景,就是别样风味。构图采取了中国画高视点、散点透视的经营方法,并且运用了中国画的线条和皴法,只是用了西洋画的工具和材料,较之中国画更强调色彩的作用而已。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的行动得到了自由,经常离开北京去外地考察、讲学、写生。一路上他用中西画法画了不少风景。这是其中一幅油画。(周昭坎文)
据庞薰琹的女儿、女画家庞涛回忆:“ 父亲不画花。因为妈妈专门画花,他认为他不如妈妈画得好。”
但自前妻丘堤女士去世后,他开始画花,而且画了很多花。画得很有心意。庞薰琹自述:“ 是不是我爱画小油画?不是。因为我的房间里,找不出比两米大的空地。是不是我爱画花?也不是。我想画人,谁敢理睬我让我画?……祇有花,有些好心人採些野花送我,我还在垃圾箱中捡些人家不要的花,我把倒头烂叶的花画得美些……” 这是蒙难的庞薰琹在苦难日子里的辛酸回忆。显而易见的,那时他画花,既是无奈,却也是精神的寄托。
他画花,不是简单的模写对象,而是根据画面需要构图变化,既依据对象,又不完全依据对象,而任凭自己的意图经营画面。他不无意地对人说:“ 有时别人送我一枝很好看的花,我就不断变换这枝花的放置位置,可以画出一簇好看的花来” ,他就是这样在苦难中找“ 乐” ,忘却了自己,把大自然赋予的一丁点美,一丁点生气,放大,升华,再现于画面,既是他高尚、乐观的情操体现,也是他于绘画艺术的奉献。
这幅《美人蕉》是他这一类花卉作品的一个典型。不难看出,整个画面(包括背景)是画家“ 设计” 的结果,花、叶陈列有致,色彩对比靓丽,富有强烈的装饰趣味。
这幅同样具有设计意味的装饰性花卉作品,在使用西洋画工具时,却运用了中国工笔花卉的精细线条,蓝灰色彩基调,衬托出了白色玉兰的温馨和生气,给人以愉悦的快感。
庞薰琹总是不停地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作画。这幅作品与《玉兰花瓶插》为同年的作品,虽然构图同具设计意味的匠心,但用色用笔就不那么细腻,而只是在绿色基调中寻找差别而显现描写对象的品格、气质。(周昭坎文)
一大把盛开的花朵插在一只宋瓷花瓶里,形式和谐完美的画面充满了装饰的美。整个画面作高调处理,色彩鲜明,构图饱满,显示出蓬蓬勃勃的生命力量。很难想像这样一幅充满生命活力的作品,却是一位不久前刚从“ 牛棚” 里放出来,还背着沉重的政治冤屈未获平反的老艺术家的手笔。
王安石曾有这样的诗句:“ 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何缘身处逆境的庞薰琹却能用自己的画笔把春色凝固于画面而永驻人间?他的一首题为《小草》的自喻诗,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注释:“ 一颗平平常常的小草,虽然饱经烈日秋风、旱涝雨雪,毕竟不可摧折,春风吹又生,始终顽强如故;甚至即使连地下的老根也枯死了,可是在死去的老根旁,却又长出新根长出了新芽,草地仍是一片绿色……”
永远乐观的信心,永不疲倦的探索,使老人永葆艺术的青春!他从不使自己笔下的花带有伤感,不论是浓彩艳丽的鸡冠花,还是淡雅飘逸的水仙花,都给人以具有生命力的美感。
诚然,庞薰琹的画花,除了寄情、言志之外,更热衷于艺术的探索。从这幅画里,我们看到画家感兴趣的不仅是关于装饰性的设计意匠,更对色彩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
他在这幅画中,可以说把对象的固有色的色相强调到极顶,全然不顾所谓环境色的制约。他认为:“ 色彩有巨大的作用” 。“ 一切器物如不加上点色彩,那么生活一定变得枯燥。” 过去士大夫阶级认为浓色不如淡色雅,淡色不如墨色高。几百年来受著这种理论的影响,使美术工作者在色彩的表现力上比较弱,在色彩的感觉上也比较迟钝。“ 不重视色彩的研究,这是非常错误的。” 他力图通过器物固有色的描绘,来提高画家对色彩的敏感和表现力。他在这幅画中,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人们:对比的固有色,可以在同一画面上取得和谐的美。而他对白色瓷瓶在高调画面上的描绘,更显示了他表现固有色的高超本领。
庞薰琹晚年画了不少水墨画。当他用强调“ 墨分五色” 的中国传统笔墨画花时,他仍然十分强调表现花的固有色。也许他认为花之所以美,正应当是它们艳丽的固有色。(周昭坎文)
丘堤《向日葵》,1947年,油画,61*50公分,庞均私人收藏。此幅作品画于1947年广州光孝寺广东艺专,丘堤与庞薰琹同时画一组向日葵静物,事后庞薰琹自认为作品没有其妻画的生动,他的那一幅画作就深藏不露了。直至近日才被发现。丘堤用笔有力、朴实、色彩绚丽。(庞均文)
庞薰琹好象很喜欢画鸡冠花,在他的作品中有好几张鸡冠花,情趣各异。有的绘画性强,有的装饰性强,有的严谨、有的洒脱。这张作于1983年的作品,把鸡冠花和吊兰画在一起,用笔轻松活泼,色彩浓艳强烈,充满活力,很难令人相信出自一位七十七岁老翁之手,这也许和他政治上得到平反、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庞薰琹的梦又获得重新编织的机会,心境愉快有关。但人们没有预料到他两年后就匆匆离开了人间,因此,有位美术评论家认为:如果庞薰琹能继续活下去,他在绘画方面将恢复年轻时代的活力,作为曾是三十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领头人,他必将在八十年代的青年美术新潮运动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使青年美术家少走不少弯路。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笔者认为庞薰琹如果活着,未必会和“ 85新潮美术” 的那些青年走在一起,正如与他同时代的洪毅然在纪念庞薰琹的文章《探索者的足迹》一文所述:“ 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实乃远远不自今日始。不过,我们那时的‘现代’概念,其内涵却与当今某些误解‘现代化’即全盘‘西方化’的人们之‘现代’概念,并不相同。我们虽然也不排除适当吸收西方艺术(包括其‘现代派’艺术)某些于我可用之形式和技法,却仍始终坚持贯彻‘中国学术现代化,外国学术中国化’之原则,既不顽固保守,复古倒退,也不亦步亦趋紧跟洋人爬行。” 老一辈的道路早已经过自己的实验而选定,而青年人是一定要亲自把西方现代绘画一百年走过的路再走一遍才会认定自己该走的路,尤其是因为大陆与外部世界封闭了四十年,庞薰琹又经过如此坎坷,青年人未必会听从他的劝导。有趣的是,洪毅然在同文中记述了庞薰琹二十年代初到巴黎,也曾于夜间,把两眼闭起来涂抹,借求意外的‘现代’效果。而当今一些青年人还把寻求‘潜意识’的灵感,当成时髦的新玩意!
此作与1983年所作鸡冠花风格完全不同。浑厚凝重,颜色用得很厚,用笔粗狂有力,构图饱满充实。
这张作品的写意风格,和《鸡冠花与吊兰》有相似之处,潇洒轻松,完全摆脱了描摹对象的拘泥,如不经意地“ 玩弄” 笔触和色彩,恰到好处地表现了生命的跃动和画家的抒情。(周昭坎文)。
(载台湾《中国巨匠美术周刊》中国系列第127期,总第227期1997.2.1)
出 版 社:台湾《中国巨匠美术周刊》中国系列
出版时间:第127期
中国现代美术的先驱庞薰琹,字虞弦,笔名鼓轩。 江苏常熟人,出身于书香门第。
江南水乡淳朴爱美的民风给予庞薰琹最早的艺术启蒙。民间刺绣的图案,枕头、帐幔上的朵朵绣花,姑娘、妇女头巾、围裙上的装饰纹样,都使他产生浓厚的兴趣,掺进自己的想像加以描绘,十岁时,便能画些工笔花鸟画。但是,为了摆脱旧家庭的束缚,他进了上海 震旦大学预科学医,只是仍然迷恋着绘画。然而,学校里的外国神父的一句话:“ 中国是出不了大画家的!"却使他毅然离开这所大学,去跟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古敏斯基的俄国人学油画。
民国八年(1919)发生的五四运动,激起青年们到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潮流。满腔热血的庞薰琹不例外,于十四年(1925)远渡重洋到巴黎学习艺术。先进敘利恩学院学素描,锻练造型能力,过一年,又进格朗·歇米欧尔研究所深造。他一方面从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法国古典派艺术进行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目接巴黎五光十色、扑朔迷离的现代绘画诸流派艺术,体味领会、进行探索,对毕卡索敢于不断改变自己作风的气魄和才华,大为倾倒。但是,当他挟着自己的创作,到巴黎一家艺术家经常聚会的古堡咖啡馆,去请教一位法国著名的批评家时,那位先生连他的作品都不看一眼,只问他对中国民族艺术有没有研究过?他回答说没有。这位批评家便说:你先回去,研究了你们祖国的传统艺术之后,再来法国,我再看你的画。批评家的这一席话,振聋发聩,使庞薰琹下了回国的决心。民国十九年(1930)他回到故乡常熟,开始钻研中国画论、画史,并和西欧美学思想进行对比,写成《薰琹随笔》,连续发表于《艺术旬刊》,记录了一个画子从东方走向西方,又从西方回归东方的种种思绪、体验和心得。
是年秋,他定居上海,创办“ 苔蒙” 画会,希望通过画会树立一种有独创精神的新艺术风格。次年,他在上海昌明美术学校任教,自己也办了一所画室,然后,又就聘于上海美专西画研究所为导师。当时,他非常看不惯那些依靠官方而自称的所谓画家,他们或师古不化的因袭,或唯西方绘画是从,毫无艺术气质。因此,民国二十年(1931),他和志同道合的倪贻德、王济远、张弦、阳太阳、杨秋人、周真太、段平右、曾志良、陈澄波等组成著名的新美术团体“ 决澜社” ,决意掀起一股与官办画会抗衡的新兴美术运动的狂澜。决澜社的《宣言》疾呼:“ 我们往古创造的天才哪里去了?我们往古光荣的历史哪里去了?……我们再不能安于这样妥协的环境之中,我们再不能任其奄奄一息以待斃;让我们起来吧!用那狂飙一样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我们以为绘画决不是宗教的奴隶,也不是文字的说明,我们要自由地、综合地构成纯造型的世界。……我们要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兴的时代精神……” 。
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庞薰琹奔波于杭州、上海,举办了四次决澜社画展。他的《地之子》即展出于第三次社展中。由于决澜社的展览,把鄙视和嘲笑掷向政客、巨贾和他们豢养的“ 官学派” 画家。因而遭致攻击、恐吓和通缉,决澜社只存在了短短的四年。但决澜社和庞薰琹对于介绍和研习西方现代绘画,推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留下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影响。
这一段时期(1930-1936年),也是庞薰琹立足本土,入流现代艺术潮流取得重要成果的阶段。他的一大批作品:《籐椅》、《裸女》、《屋顶》、《绿樽》、《在画室中》、《地之子》、《无题》、《人生哑謎》、《如此上海》、《如此巴黎》等,成为我国早期现代艺术的代表作,展现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形式和精神。遗憾的是由于社会的动荡、时代的变迁和个人的遭际,庞薰琹中断了这种具有时代精神的现代艺术的探索,转而把精力集中于工艺美术方面,尽管他于这方面的努力,最终为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建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教学体系,但对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
庞薰琹在法国留学期间,适逢十二年一遇的万国博览会的举行。外国工商美术的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即已萌芽了将来一定要建立一所中国人的工艺美术学校的理想,并且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回国以后,他曾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创办了“ 大熊工商美术社” ,举办了一次“ 工商美术设计展览会” ,开展广告和工艺美术设计业务,但却因外国广告公司的排挤而不能立足。因此,二十五年(1936)他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时,说服校方开设“ 工商美术课” ,企望培养出一大批足以与外国人竞争的装潢设计人才,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工艺美术体系。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南迁,计划落空。
民国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38-1940),庞薰琹在云南昆明担任中央博物院研究员,致力于民族工艺美术的研究,在云、川各地考查研究了大量古代陶、铜、石器工艺图案纹样和少数民族服饰图案,编绘了《中国图案集》四册和《工艺美术集》。三十年至三十六年(1941-1947),他先后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和中山大学任教。从事工艺美术教学,编绘了《工艺美术设计图案》。期间,他曾于三十年和三十二年(1941和1943)在成都、重庆举办四次个展,分别展示他过去的创作和后来多用毛笔画的少数民族题材和唐装舞女图,风格各异。
1949年后,他先后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杭州)和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3年,周恩来委托他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全力以赴,组织力量进行社会调查、收集民族、民间工艺美术遗产,进行整理、研究、展览、出版,并到苏联进行考察,终于用他的辛劳和汗水,于1956年建成中国第一所多学科、综合性的高等工艺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出任第一副院长。但不久,即于1957年“ 反右” 运动中蒙垢成为右派分子,被解除了副院长职务,除教书外,闭门著作,历20年写成《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直至1979年平反,至1980年恢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职务。从1949年到1972年,23年中他仅画了《鸡冠花》等5幅小油画,1973年才开始重新执笔画些花卉作品,有油画也有国画,装饰性和绘画性、写实和写意融为一体,清新淡雅,但却流露出“ 超脱” 的寂寞,已经迥异于四十多年前“ 前卫” 的庞薰琹了。
1985年3月18日清晨,庞薰琹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9岁。
庞薰琹早在巴黎时就对工艺美术的图案设计感兴趣。回国后,收集了上千幅中国古代青铜、陶瓷、丝绸和漆器上的纹样,并于此基础上在四川郫县创作了一本《工艺美术设计》,1944年交友人带到国外出版,辗转三十余年后,由英国美术史论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带回北京交还庞薰琹,198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四幅方盒图案设计是1940年在昆明创作的《中国图案集》100种设计中的四种,也是以古代纹样变形手法设计,曾在昆明展览,获学术界高度评价。
青年时代的庞薰琹激烈地反对刻板机械地模仿“ 自然主义” 和所谓“ 写实派” 的绘画。他认为这种模仿自然的绘画,在现代“ 以数秒钟的时间拍一张照相,不会较描写数个月的一幅少真实。” 由此,他主张艺术家应该利用各自的技巧,自由地、自然地表现事物和自我。他的艺术主张,在《决澜社宣言》中更表白得十分明确:“ 我们厌恶一切旧的形式,旧的色彩,厌恶一切平凡的低级的技巧。我们要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时代的精神。……野兽派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 达达派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二十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出现一种新兴的气象了。”
1932年前后创作的《如此巴黎》、《如此上海》、《人生的哑謎》、《画室内》和1938年创作的《路》,有别于同时期创作的《地之子》、《三个女性》那种沉静的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力图用激烈的绘画语言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绪。用庞薰琹自己的说法是“ 我的一生,是探索探索再探索的一生。” 他一直在尝试用各种手法表现不同的主题。
在《如此巴黎》这幅作品中,画家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形象,用“ 蒙太奇” 手法剪辑,以现代构成方法处理构图,将繁华而疯狂的夜巴黎浓缩在一个画面上,卖笑的女人、赤裸的身体、愁苦的眼神、叼雪茄的男人、隐现的警察、摇曳的灯光、眩目的广告,便是一扇门、两扇窗和几张纸牌,也在时刻变幻着。
《如此上海》、《人生哑謎》采取了相同的手法,表现了类似的内容,可以认为是画家于这一时期思考社会现象的一组系列画。这组作品的表现手法虽然未脱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影响,但是,在形象、色彩方面具有装饰性,显然较为接近东方人的审美情趣,错综复杂和组合却不失谐和自然,激烈变幻的表现却不失平衡合理。
庞薰琹在年轻时代,尝试了西方绘画各种流派的画法,最后选择了从西方回归东方的艺术道路。他在尝试各种新画法时,并不是简单地模仿抄袭,而是溶入了他自己对描绘对象和适合这一对象的表现方法的理解,所以,他的用笔自然、流畅、没有造作的痕迹。这幅《籐椅人体》是他最得意的一幅早期作品。虽然是一幅学习马蒂斯风格的习作,但其神韵不失大师风范、简炼到多一笔即为添足的线条、洒脱流畅;夸张的变形也是到了极致,头部的大小尽管和腿的比例失调,但是,再大一点或者再小一点,这幅画就没有美学价值;籐椅的黄色和人体的肉色非常接近,同样也是调色板上多一分别的颜色配比,就会失去这种和谐的对比。这幅画过去很少有机会与读者见面。因此特地介绍。可惜原作已不复存在。据画家的女儿庞涛(也是一位著名女画家),抗日战争爆发时,从北平带出的一卷三十年代的作品,总共有20多幅,这一幅也在其中,而现在祇剩下了《法国老人像》一幅。
这是庞薰琹有感于当年江南大旱,土地龟裂,民不聊生而花了几个月时间创作的一幅作品,本是一幅油画,曾于1932年他在上海举行的首次个人展览及在第三次决澜社作品展览中展出,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展出时曾轰动一时,但后来被当局认为有“ 赤化宣传” 嫌疑,受到攻击,他本人收到匿名恐吓信,不久,法租界巡捕还准备缉捕他,他在傅雷的帮助下逃到了杭州躲避。据说这幅画后来由四川博物馆收藏,但又转手一家外国博物馆买去。现在这幅是1934年用水彩画复制的,原作也已散失(编者注:水彩画原作现藏庞薰琹美术馆)。
画面上是一个将死的僵硬孩子,横卧在一个农民模样的男人手中,这个男人一手扶着孩子,一手握拳;孩子的母亲俯首靠在丈夫的肩上,掩面而泣。他们穿戴整齐,看上去体质健康。据画家自述,他是用这对健美的青年夫妇来象征中国,而用将死未死的孩子隐喻当时的中国人民。
无疑,画家是充满感情完成这幅油画的。据说,他回到常熟家乡,亲眼看见农民把地契贴到地主的大门上,便全家离乡背井逃荒而去,庞薰琹含着同情的泪水创作了这幅画,他试图采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来创造一幅主题是中国总有一天会摆脱贫困的作品。
我们注意到画家创作的是一种被压抑而又平静的人物情感。他采用简化和拉长了的形体描绘,大面积平涂,以平面、装饰的风格来表现朴实和力量,十分成功。这种风格不由使人联想到毕卡索蓝色时期的作风。画家承认他最佩服的就是毕卡索。但他决不是模仿和照搬。他主张“ 中国学术现代化,外国学术中国化” ,他吸收外来形式,却注入了中国人的情感、神韵,包括造型的线条的运用。可惜像《地之子》这样具有时代博大宏伟精神和深刻内涵、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作品并不多见。
在庞薰琹的作品中,有几幅以他生活历程中关系重大的几处住处景象为题材所作的风景画,是反映画家真实心情的精心佳作。这幅《白家庄旧居雪景》,有人认为是画家政治上蒙冤后所作的第一幅作品,阴冷、 滞凝、沉重的情调,反映了他被免职后打发到东郊白家庄两间斗室离群鳏居的忧愤、委屈、迷惘的心情。
其实仔细分析这幅画面的情调并非如此。厚重白雪覆盖的新兴城郊,虽然冷清,但一片微弱温暖的阳光映照着新建的住宅,如同同一时期画家在白家庄斗室里画的那些花卉,透露出的是一样的乐观和富有生机。庞薰琹本是一个乐观豁达的艺术家。当他刚搬到白家庄时,固然因为蒙冤、妻子丘堤去世,使他一月间黑发全白,病至垂危。但经一位老中医点化,知医药无效,全靠自我解愁,于是拿起搁置画笔开始画花,心情逐渐开朗,病渐痊癒。1962年,他又与袁韵宜女士结婚,领一女,生活重新有了信心。因此,他那时虽因作为“ 摘帽右派” ,担任教学工作中仍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发生,但心情上总还是乐观的。因此,对于这幅画的解释应是困苦中仍然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冬天过去即是春天。
不管如何解释画家作此画时的心情,这幅画的构图、色彩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幅经典之作。画面上横的和直的线条分割、冷的和暖的色彩对比,既合理而又巧妙,显示了画家的功底和机智。
1942年,庞薰琹深入到“ 地无三里平” 的贵州山区,当地土著居民的歌舞和淳朴的性格、健壮的体格、欢快自立的精神,极大地吸引了他。他踏遍八十多个苗家村寨,用他的画笔创作了二十幅《贵州山民图》。《橘红时节》便是其中的一幅。庞薰琹在创作《贵州山民图》时,选择了一种适合表现个性特征的独特艺术形式,那是中西绘画融合成有机整体的崭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标志着他是在与法国的传统决裂中探索着自己的艺术道路,因而有的批评家称这批作品为“ 他的艺术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 。为此,其中10幅为英国皇家协会收藏,其余则为中国美术馆所珍藏。
从《橘红时节》这幅画上可以看出,画家将画面作了高度平面化和装饰化的处理,写实和变形结合起来,具体的人物形象和非具体的装饰图案结合起来,再现客观对象和表达主观情感结合起来,作品艺术形式和谐完美,从形式美的外表迸发出艺术家心灵深处的激情。同这一时期不少效力于融合中西绘画技巧的画家相比较,庞薰琹无疑走在这支队伍的前列。香港的高美庆博士在《20世纪的中国绘画》一书中如此评论庞薰琹的这批作品:“ 线条的运用与赋予图案性造型,使他这类作品具有一种柔和、优美的魅力和极强的装饰性。……庞薰琹是透过中西艺术合壁,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
诚然,面对开发一种不曾有过的新的审美观念的确立,道路是不平坦的。恰如画家在《自剖》(1943年)一文中所述:“ 我所描写的贵州的同胞,无容讳言,与实际的他们离得很远。不能拿民族学的尺寸来量它。因为笔下总不免流露出自己。可是服饰方面,曾尽量保存它原来面目,因此,给我不少束缚,……” 。[庞薰琹认为,这些装饰图案是苗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是表达他们艺术的一个丰富多彩的方面,是苗族人民生活的一个特色。在他的创作中,苗族装饰艺术和苗族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祇有引用和发展到工艺美术中去的时候,它才是孤立存在的。]
背篓
继于四十年代初完成二十幅《贵州山民图》之后,庞薰琹于1946年回到上海,又以同样的手法,以苏南农民为对象,创作了水彩画《背篓》、《小憩》、《捉鱼》、《割稻》等作品。《背篓》是其中最精彩的一幅。
这幅作品,造型的真实和写意结合,形意兼备。
和画贵州苗民的服饰一样,画家刻意细致地描绘了印花布衫的图案,但与苗民图不同的是,这种刻意的描绘也用于背篓的编紮和作为背景的树叶的描绘,因此,少了原先那种生硬拼贴的感觉,从而成为一幅完整的、富有装饰趣味的作品。
同时,于人物神情的刻划,庞薰琹也下了更大的功夫,温柔、内秀的气质和健美、勤劳的外在体形结合,塑造了完美的东方女性形象,尤其是眉宇间含蓄的表情描写,很有些东方蒙娜丽莎的意味,十分耐人咀嚼。
庞薰琹此系列的创作于重庆展出时颇引出一番争议,有人批评他画“ 美人儿” 或“ 唯美主义” ,更有人贬为“ 多少带些低能的趣味主义的东西。” 但庞薰琹在《自剖》中反驳道:“ 十多年前读邓肯的自传,看惠格曼的表演,又曾数次仔细参观印度尼奥太·依奥迦的舞蹈,自那时起在我胸中时时起伏种种幻象。我曾有过这样痴愿,想研究已绝亡的汉族的‘舞’,可惜环境、时间、精神,都不允许我实行我的理想。近年来,我的兴趣又转到古代的图案,连带对于服饰也发生了兴趣,……所以,我用手边有限得很的资料,凭我的想像作此舞装。……现在赶快去研究还来得及找到一点贫乏的参考,不然连一点贫乏的参考,也会被时间消灭了的。为保存中国的文化著想,不见得是无所谓吧!” 现在看来,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民族危亡关头,一些人对艺术家提出苛刻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学者的庞薰琹想的是做学问,不免显出十足的书生气,因此,他的这组作品不免不合时宜。而于半个世纪后再看这些创作,诚如英国美术史论家苏立文于《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一书中所述:“ 他的精神系列画‘舞蹈者’,渊源于他对唐代艺术与服饰的研究,也同样引人入胜。这些作品尽管使用的是中国画笔,在其理想化的加工中,透露出对西方艺术的熟稔。” 确实,从这组作品里,我们感受到了盛唐风范,却也觉察到了那个时代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而在表现技法上还可以隐约觉察日本浮世绘的趣味,而当庞薰琹还在巴黎的时候,欧洲现代画派大师们正对日本浮世绘崇拜得五体投地,苏立文所指的“ 西方艺术的熟稔” 也许指的就是这一点,不少欧洲现代派画家都临摹过浮世绘。
尽管对这组画的舆论褒贬不一,不过庞薰琹却斩钉截铁地声明:“ 似乎因为我画这些唐装,有人就说我画‘美人儿’。这新的‘头衔’,我祇能拒谢。我不单不是唯美主义者,而且我也反对唯美论。这类作品我第一次试作,但也将成为这类作品的最后一次试作。” 不过,1946年,傅雷为他举行第六次个人展览时,非常佩服他的“ 铁线” 钩勒技巧,所以一再希望他能展出这些作品,因此他复制了几幅带彩的。这一幅就是其中之一。1983年,这些作品又一次在纪念他执教五十二周年时于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庞薰琹画展》中展出。
这幅画记录的也是画家于四十年代在四川郫县的旧居,但这是一幅构图和色彩奇巧的佳作。
庞薰琹一再说过:“ ……如果,我的作品能使你感到一点美感,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他确实如此对待他的每幅作品。在平凡中发现美,然而加以表现,把美奉献给人们。
在这幅画的画面上,一片小小的竹林,一幢平常的木屋,经他妙手经营,给人无比温馨。他巧妙地将19根竹枝、8根树杆和10根房柱,用5根椽梁和一排窗户加以分割,应用的仍是他所熟稔的现代构成分割的原理,但那么自然、机巧。无怪乎,有位批评家评述他的作品:有古典主义的和谐、完整、庄重与肃穆;有浪漫主义的诗情;有写实主义的诚实;有表现主义的虚灵;有印象主义的率真;有一切形式主义的智巧。就在这么一幅小小的风景画里,我们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竹林的宁静。画家就在这幢房子里整理着他收集来的许许多多古代纹样,设计着中国工艺美术的未来。这幅画现在由画家的妹妹收藏于上海的家中。
据庞薰琹的女儿、女画家庞涛回忆:“ 父亲不画花。因为妈妈专门画花,他认为他不如妈妈画得好。”
但自前妻丘堤女士去世后,他开始画花,而且画了很多花。画得很有心意。庞薰琹自述:“ 是不是我爱画小油画?不是。因为我的房间里,找不出比两米大的空地。是不是我爱画花?也不是。我想画人,谁敢理睬我让我画?……祇有花,有些好心人採些野花送我,我还在垃圾箱中捡些人家不要的花,我把倒头烂叶的花画得美些……” 这是蒙难的庞薰琹在苦难日子里的辛酸回忆。显而易见的,那时他画花,既是无奈,却也是精神的寄托。
他画花,不是简单的模写对象,而是根据画面需要构图变化,既依据对象,又不完全依据对象,而任凭自己的意图经营画面。他不无意地对人说:“ 有时别人送我一枝很好看的花,我就不断变换这枝花的放置位置,可以画出一簇好看的花来” ,他就是这样在苦难中找“ 乐” ,忘却了自己,把大自然赋予的一丁点美,一丁点生气,放大,升华,再现于画面,既是他高尚、乐观的情操体现,也是他于绘画艺术的奉献。
这幅《美人蕉》是他这一类花卉作品的一个典型。不难看出,整个画面(包括背景)是画家“ 设计” 的结果,花、叶陈列有致,色彩对比靓丽,富有强烈的装饰趣味。
一大把盛开的花朵插在一只宋瓷花瓶里,形式和谐完美的画面充满了装饰的美。整个画面作高调处理,色彩鲜明,构图饱满,显示出蓬蓬勃勃的生命力量。很难想像这样一幅充满生命活力的作品,却是一位不久前刚从“ 牛棚” 里放出来,还背着沉重的政治冤屈未获平反的老艺术家的手笔。
王安石曾有这样的诗句:“ 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何缘身处逆境的庞薰琹却能用自己的画笔把春色凝固于画面而永驻人间?他的一首题为《小草》的自喻诗,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注释:“ 一颗平平常常的小草,虽然饱经烈日秋风、旱涝雨雪,毕竟不可摧折,春风吹又生,始终顽强如故;甚至即使连地下的老根也枯死了,可是在死去的老根旁,却又长出新根长出了新芽,草地仍是一片绿色……”
永远乐观的信心,永不疲倦的探索,使老人永葆艺术的青春!他从不使自己笔下的花带有伤感,不论是浓彩艳丽的鸡冠花,还是淡雅飘逸的水仙花,都给人以具有生命力的美感。
诚然,庞薰琹的画花,除了寄情、言志之外,更热衷于艺术的探索。从这幅画里,我们看到画家感兴趣的不仅是关于装饰性的设计意匠,更对色彩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
他在这幅画中,可以说把对象的固有色的色相强调到极顶,全然不顾所谓环境色的制约。他认为:“ 色彩有巨大的作用” 。“ 一切器物如不加上点色彩,那么生活一定变得枯燥。” 过去士大夫阶级认为浓色不如淡色雅,淡色不如墨色高。几百年来受著这种理论的影响,使美术工作者在色彩的表现力上比较弱,在色彩的感觉上也比较迟钝。“ 不重视色彩的研究,这是非常错误的。” 他力图通过器物固有色的描绘,来提高画家对色彩的敏感和表现力。他在这幅画中,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人们:对比的固有色,可以在同一画面上取得和谐的美。而他对白色瓷瓶在高调画面上的描绘,更显示了他表现固有色的高超本领。
庞薰琹好象很喜欢画鸡冠花,在他的作品中有好几张鸡冠花,情趣各异。有的绘画性强,有的装饰性强,有的严谨、有的洒脱。这张作于1984年的作品,把鸡冠花和吊兰画在一起,用笔轻松活泼,色彩浓艳强烈,充满活力,很难令人相信出自一位七十七岁老翁之手,这也许和他政治上得到平反、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庞薰琹的梦又获得重新编织的机会,心境愉快有关。但人们没有预料到他两年后就匆匆离开了人间,因此,有柆美术评论家认为:如果庞薰琹能继续活下去,他在绘画方面将恢复年轻时代的活力,作为曾是三十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领头人,他必将在八十年代的青年美术新潮运动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使青年美术家少走不少弯路。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笔者认为庞薰琹如果活着,未必会和“ 85新潮美术” 的那些青年走在一起,正如与他同时代的洪毅然在纪念庞薰琹的文章《探索者的足迹》一文所述:“ 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实乃远远不自今日始。不过,我们那时的‘现代’概念,其内涵却与当今某些误解‘现代化’即全盘‘西方化’的人们之‘现代’概念,并不相同。我们虽然也不排除适当吸收西方艺术(包括其‘现代派’艺术)某些于我可用之形式和技法,却仍始终坚持贯彻‘中国学术现代化,外国学术中国化’之原则,既不顽固保守,复古倒退,也不亦步亦趋紧跟洋人爬行。” 老一辈的道路早已经过自己的实验而选定,而青年人是一定要亲自把西方现代绘画一百年走过的路再走一遍才会认定自己该走的路,尤其是因为大陆与外部世界封闭了四十年,庞薰琹又经过如此坎坷,青年人未必会听从他的劝导。有趣的是,洪毅然在同文中记述了庞薰琹二十年代初到巴黎,也曾于夜间,把两眼闭起来涂抹,借求意外的‘现代’效果。而当今一些青年人还把寻求‘潜意识’的灵感,当成时髦的新玩意!
未圆的梦
有人把庞薰琹称为“ 中国前卫艺术之父” ,因为在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程产生历史性影响的三位同时代画家中,他既区别于徐悲鸿立足本土、选择写实绘画来超越中国传统绘画的价值体系,又不同于林风眠以中西艺术的调和来确立新的艺术价值体系,而是中国画家中,最早入流西方现代艺术潮流,把价值取向定位于前卫艺术而回归本土的一位先驱画家。可惜的是,这位本可以成为中国第一位前卫艺术大师的天才画家,他的才华却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中被扼制,从四十年代开始就转而从事工艺美术,留下了一个未圆的“ 薰琹的梦” 。
薰琹的梦
著名翻译家和美术批评家傅雷于民国二十一年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的开幕,曾于《艺术旬刊》发表一篇题为《薰琹的梦》的文章来分析庞薰琹的创作之路。文章说:“ 他从童年时无猜的梦,转到科学的梦非所梦,音乐的梦其所梦,至此,即开始创造他的《薰琹的梦》。” 庞薰琹的“ 梦” 是怎样编织起来的呢?除了震旦大学那位外国神父说“ 中国是出不了大画家” 的刺激外,当时中国画坛的衰微更促使庞薰琹要成为一位改变中国现代美术面貌的斗士。当他到了巴黎“ 一切新的,旧的,醜的,美的,看的,听的,古文化的遗迹,新文明的气焰,自普恩克尔(Poincare)至Josephine Baker都在他脑中旋风似的打转、打转。他,黑丝绒的上衣,帽子斜在半边,双手藏在裤袋里,一天到晚的,迷迷糊糊,在这世界最大的漩涡中梦著……。” (傅雷:《薰琹的梦》)终于他作出了选择,放弃了进“ 学院派” 统治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的机会,而进了位于巴黎艺术活动中心蒙巴拉斯(Montparnasse)的格朗歇米欧尔研究所(La Grand Chaumiere)学习,因为在那里他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新派艺术家如“ 巴黎画派” 中毕卡索、凡童根(Van Dongen)、古斯林、尤特里罗(Utrillo)、雕塑家布尔德尔(Bourdelle)等人和其他新潮文学家、舞蹈家、艺评家的谈艺说文,学到许多从学院里学不到的东西,不仅窥见了许多人盛名背后的虚华,也感受到了一些现代画派画家的质朴的淳厚,他尤其崇拜毕卡索的勇气、才华和气魄。
无疑,参观十二年一遇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也给他的梦凭添一份创造的色彩。他感到建筑风格和装饰艺术风格正在影响着时代风格的变化,由此改变了他纯绘画艺术的观念。民国十七年(1928),他还到德国考察了受包豪斯影响的建筑和艺术,接受了融建筑、雕塑、绘画为一体的包豪斯思想。这对他日后创作中的装饰风格和工艺美术设计,起了一辈子的影响。当他看到一个高水平的日本画展在巴黎的轰动之后,又受到古堡咖啡馆那位权威批评家的指点,他深信“ 从哪种土壤里出来的芽,也祇能在同样的土壤里生长、开花、结果。” (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于是带着西方前卫艺术意识,决心回归本土演绎他的“ 薰琹的梦” 。
决澜社时期
回到祖国,他“ 梦一般观察” ,“ 梦一般寻思” ,“ 梦一般表现” ,“ 他把色彩作纬,线条作经,整个人生作材料,织成他花色繁多的梦。他观察、体验、分析如数学家,他又组织、归纳、综合如哲学家。他分析了综合,综合了又分析,演进不已;” “ 他变形,因为要使‘形’有特种表白,这是Defornisme espressive。他要给予事物以某种风格,因为他的特种心境(Etada’me)需要特种典形来具体化。” “ 他以纯物质的形和色,表现纯幻想的精神境界;” “ 然而在超现实的梦中,就有现实的憧憬,就有时代的反映。” “ 我们一般自命清醒的人,倒不如站在现实以外的梦中人,更能识得现实。” 傅雷对《薰琹的梦》的剖析,概括了庞薰琹三十年代“ 决澜社时期” 全部创作的艺术特点和艺术价值,十分精辟。在决澜社时期,庞薰琹不仅是中国早期现代艺术运动的组织者,更是推进中国早期现代艺术骁勇的主将,短短几十年中,他推出众多作品,展示了中国早期现代艺术的形式与精神。如果说他的《西班牙舞》、《藤椅》、《女裸》、《屋顶》等作品还存留着西方现代流派的余韵,《在画室中》、《丘堤像》等作品以现代美术形式构成融入东方情韵的装饰绘画语言,那么,他的《地之子》、《无题》、《人生哑謎》、《如此上海》、《如此巴黎》和《路》,则借鉴了西方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的表现形式和艺术精神,把他回国后亲身感受到的社会现实和他忧国忧民的思绪,通过超时空的现代形式构成尽收进他的画面。誠如陶咏白《对庞薰琹的历史思考》一文所指出:“ 他的作品与同一时代的徐悲鸿用写实手法画的《田横五百士》、与林风眠用表现主义手法画的《人道》、《痛苦》等主题画相比较,具有异曲同工的社会功效。” “ 庞薰琹的作品较之徐悲鸿用历史故事来影射现实更贴近生活。他与林风眠一样是重主观表现型的画家……。林风眠注重情感抒发中赋予画面大的运动节奏的美感……使画面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庞薰琹则在理性的组织画面中追求着装饰美感,并赋予其更深广的内涵而发人深思。”
无疑,庞薰琹于“ 决澜社” 时期的创作,是他艺术道路上最光彩的一页,它突破了中国美术的审美传统,点燃了时代审美精神的火花。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星火花未能成炬,但过了半世纪以后,这一星火花仍然激励起中国的青年美术家们举起火炬,大步迈向庞薰琹所选择的价值目标!
梦的转折
决澜社的被迫解散,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流亡生活,使庞薰琹的艺术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诚如他的《自剖》所述:“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渺小的我在这个时期,一步紧一步地感到惶恐,我虽想全身投入东西方文化的怀抱,不过我太渺小了。也许,我祇能像流沙一般,被洪流吞没……。” 他中断了具有时代博大宏伟精神和深刻内涵的前卫绘画艺术的探索,他忍受不了前卫艺术在中国这块特殊的文化土地上的孤独,同时又深感于此民族危亡的时代,艺术不是表现“ 自我” 和强调“ 个性” 的宠儿,“ 现在我以为写黑暗不如写光明;人生需要艺术,艺术能给人以鼓励……这伟大的时代使我渐渐忘了小我,也许我能步入另一个境界……。” (《自剖》)他深入到“ 地无三里平” 的贵州山区苗寨用毛笔画了一幅幅《苗家女》,完成了20幅《贵州山民图》和一批唐装舞女图。这些画,他作了高度平面化和装饰化的处理,写实和变形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虽不如决澜社时期作品那样洒脱、奔放,但在艺术形式上比较和谐完美,在掌握传统绘画技巧线描方面,趋向老到成熟。然而这些作品又流露出了画家在艺术思想转变过程中进行探索的种种苦恼。“ 我爱沉思,我爱冷静的头脑……我爱毕卡索,于是,我爱火热的心。甚而至于我爱炸弹。我当然不是爱他的残忍,我爱他的外表又笨又冷,在这笨和冷的外衣中裹着火热的心。这种种爱好,就是组织成我画面的源泉。” 但是,显然他在这样的探索中感到“ 苦闷而又低能!(引文均自《自剖》)整个四十年代,他就处于这种转折斯的探索中,《背篓》、《橘红时节》、《情话》、《笙舞》等作品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来不及重圆的梦迹
四十年代的开始,庞薰琹就为实现另一个梦,即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的、现代的工艺美术学校而注入他越来越多的心血,这一努力明显地反映于他的绘画创作里,在一幅幅反映苗民生活的作品中,他详实的记录了苗民的服饰图案,甚至于不顾由此而使画面产生拼贴感。进了五十年代,他几乎停止了创作,全身心地投入创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及其教学理论体系的工作,并于1956年实现了这个梦,却又于翌年反右运动中砸碎了这个梦。当他二十年后又有机会重圆这个梦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遭到十年政治动乱破坏后的中央工艺美院,尽管他以七十高龄的耆耄之躯加倍奋力工作,然而,时间已经不夠了,他匆匆离开了人世。绘画本来就是庞薰琹的生命之源,它神奇地使庞薰琹摆脱了疾病和苦恼,又重新生活在自己构筑起来的诗意中。他在鳏居多年后又结了婚,有了女儿。如他平反后写的一首诗所述:“ 二十二年这样长的时间会留下一些痕迹/在我身上是一头白发/满身疾病/可是在我胸膛中/有一颗火热的心/它在跳/现在跳得那么激动/它又跳得那样平稳/过去就让它过去吧/现在还是向前看吧!” 他在编写《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一书的同时,不停地用油画在室内画花,百合花、美人蕉、鸡冠花、白菊花、牵牛花……朋友们给他一枝花,他得意地画成一簇花,他把悲哀留在心底,把美好留给人间,他把自己无私、乐观的人格情操倾注于他的花的系列作品中,每一幅《花》,无不流露出清新、平和的意蕴,表达了画家淡泊明志的情趣。综观庞薰琹于蒙难时期和政治上获得平反以后的一系列花和风景的创作,虽然已不见他青年时期作品那种用笔大刀阔斧,具有深刻内涵和冲击力的作风,但仍见他不疲倦地运用现代现式规律,力求在平凡的画面上求得审美观念的突破,色彩和肌理的处理非常精美,集装饰性和绘画性为一体,有许多作品的色彩、构图、肌理、形式处理,堪称经典。评论家认为:如果这些作品不是在身处逆境或平反后“ 心有余悸” 的情况下产生,一定会更少拘泥;而他如果能多活二十年,必将重新成为中国一代前卫艺术的巨匠。可惜的是:生不逢时!薰琹的梦是个未圆的梦。
庞薰琹作品解读
庞薰琹早在巴黎时就对工艺美术的图案设计感兴趣。回国后,收集了上千幅中国古代青铜、陶瓷、丝绸和漆器上的纹样,并于此基础上在四川郫县创作了一本《工艺美术设计》,1944年交友人带到国外出版,辗转三十余年后,由英国美术史论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带回北京交还庞薰琹,198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四幅方盒图案设计是1939年在昆明创作的《中国图案集》100种设计中的四种,也是以古代纹样变形手法设计,曾在昆明展览,获学术界高度评价。
庞薰琹1940年设计的《工艺美术集》将中国古代纹样与现代设计意识相结合,创造性的开辟了一条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设计道路,至今影响深远。这批设计作品,在阔别了三十余年之后,由好友牛津大学教授苏立文从英国带回北京。但遭阻无法见面,数次之后才得机会,完璧归赵,亲自交到庞薰琹手中。原作崭新如初。时隔不多日,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将其出版,然而这批珍藏的精品,竟然被直接送到工厂制版,一本小小的工艺美术设计出版之后,原作被污损到了不堪入目之地步,庞薰琹再次见到自己这批作品时,亦奈何不得。(庞均撰文)
晚年的庞薰琹进敦煌、下江南、去山东考察和讲学,一路画了不少小幅写意风景,别具一格,用笔简练洒脱,颇有韵味。(周昭坎撰文)
青年时代的庞薰琹激烈地反对刻板机械地模仿“ 自然主义” 和所谓“ 写实派” 的绘画。他认为这种模仿自然的绘画,在现代“ 以数秒钟的时间拍一张照相,不会较描写数个月的一幅少真实。” 由此,他主张艺术家应该利用各自的技巧,自由地、自然地表现事物和自我。他的艺术主张,在《决澜社宣言》中更表白得十分明确:“ 我们厌恶一切旧的形式,旧的色彩,厌恶一切平凡的低级的技巧。我们要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时代的精神。……野兽派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 达达派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二十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出现一种新兴的气象了。”
1932年前后创作的《如此巴黎》、《如此上海》、《人生的哑謎》、《画室内》和1938年创作的《路》,有别于同时期创作的《地之子》、《三个女性》那种沉静的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力图用激烈的绘画语言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绪。用庞薰琹自己的说法是“ 我的一生,是探索探索再探索的一生。” 他一直在尝试用各种手法表现不同的主题。
在《如此巴黎》这幅作品中,画家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形象,用“ 蒙太奇” 手法剪辑,以现代构成方法处理构图,将繁华而疯狂的夜巴黎浓缩在一个画面上,卖笑的女人、赤裸的身体、愁苦的眼神、叼雪茄的男人、隐现的警察、摇曳的灯光、眩目的广告,便是一扇门、两扇窗和几张纸牌,也在时刻变幻着。
《如此上海》、《人生的哑謎》采取了相同的手法,表现了类似的内容,可以认为是画家于这一时期思考社会现象的一组系列画。这组作品的表现手法虽然未脱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影响,但是,在形象、色彩方面具有装饰性,显然较为接近东方人的审美情趣,错综复杂的组合却不失谐和自然,激烈变幻的表现却不失平衡合理。
《人生的哑謎》傅雷说庞薰琹以艺术家无猜(Innocent)的童心,再现了人生的梦,是明白地悟透了之后造出的清醒的假梦,是从现实中提炼出若干形而上的要素,在探求人生之哑謎。所以虚幻的画面反映的是真实的人生,表达的是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周昭坎撰文)
这幅油画作于巴黎,画得很轻松,颜色调得很稀薄,画面也没有塗满,有的地方如衣褶,如画中国画一般,一鉤了之。他认为油画的画法不应有定规,严谨的古典画法或塗鸦式的信笔作画,如同书法的蝇头小楷与狂草,各有千秋。(周昭坎文)
(另附庞均《自画像》1993年,65*53公分)庞氏一门为浑然天成的艺术之家。庞薰琹与其子庞均皆为天才型的创作者,但因时代的变动,使得庞薰琹的创作生涯历经几多波折。庞薰琹此画作于其逝世前两年,其眉宇间内斂而历尽沧桑,仿佛是抒发时不我予的嗟叹。(林妙玉撰文)
庞薰琹在年轻时代,尝试了西方绘画各种流派的画法,最后选择了从西方回归东方的艺术道路。他在尝试各种新画法时,并不是简单地模仿抄袭,而是溶入了他自己对描绘对象和适合这一对象的表现方法的理解,所以,他的用笔自然、流畅、没有造作的痕迹。这幅《籐椅人体》是他最得意的一幅早期作品。虽然是一幅学习马蒂斯风格的习作,但其神韵不失大师风范、简炼到多一笔即为添足的线条、洒脱流畅;夸张的变形也是到了极致,头部的大小尽管和腿的比例失调,但是,再大一点或者再小一点,这幅画就没有美学价值;籐椅的黄色和人体的肉色非常接近,同样也是调色板上多一分别的颜色配比,就会失去这种和谐的对比。这幅画过去很少有机会与读者见面。因此特地介绍。可惜原作已不复存在。据画家的女儿庞涛(也是一位著名女画家)回忆,抗日战争爆发时,从北平带出的一卷二、三十年代的作品,总共有20多幅,这一幅也在其中,而现在祇剩下了《法国老人像》一幅。
安玛瑞儿(Tarsila do Amaral ),"Abaporu",1928年,油画。在二十世纪初,一群来自拉丁美洲的艺术家蜂涌至巴黎习画。如同庞薰琹一般,这些艺术家身处于西方美学观念主导的冲击后,经过一番审思之余,最后泰半在追溯根源及对自身文化认同的过程里落叶归根。巴西女画家安玛瑞儿即是一例。此画融合了当时主流画派的立体主义与超现实派别的表达意识,以简单而夸张的造型,表达出对其特有文化的孺慕与崇敬。于此所有欲被阐述的对象,其造型都被约简到最单纯的地步,没有一丝丝多余累赘的线条来干扰构图所欲传达的讯息。图中主体休息于地面,象征着与土地之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其粗硕的四肢和细小得不成比例的头部及模糊的五官,与庞薰琹的《滕椅人体》颇有相似之感。(林妙玉文)
这是庞薰琹有感于当年江南大旱,土地龟裂,民不聊生而花了几个月时间创作的一幅作品,本是一幅油画,曾于1932年他在上海举行的首次个人展览及在第三次决澜社作品展览中展出,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展出时曾轰动一时,但后来被当局认为有“ 赤化宣传” 嫌疑,受到攻击,他本人收到匿名恐吓信,不久,法租界巡捕还准备缉捕他,他在傅雷的帮助下逃到了杭州躲避。据说这幅画后来由四川博物馆收藏,但又转手一家外国博物馆买去。现在这幅是1934年用水彩画复制的,油画原作已散失(编者注:水彩画原作现藏庞薰琹美术馆)。
画面上是一个将死的僵硬孩子,横卧在一个农民模样的男人手中,这个男人一手扶着孩子,一手握拳;孩子的母亲俯首靠在丈夫的肩上,掩面而泣。他们穿戴整齐,看上去体质健康。据画家自述,他是用这对健美的青年夫妇来象征中国,而用将死未死的孩子隐喻当时的中国人民。
无疑,画家是充满感情完成这幅油画的。据说,他回到常熟家乡,亲眼看见农民把地契贴到地主的大门上,便全家离乡背井逃荒而去,庞薰琹含着同情的泪水创作了这幅画,他试图采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来创造一幅主题是中国总有一天会摆脱贫困的作品。
我们注意到画家创作的是一种被压抑而又平静的人物情感。他采用简化和拉长了的形体描绘,大面积平涂,以平面、装饰的风格来表现朴实和力量,十分成功。这种风格不由使人联想到毕卡索蓝色时期的作风。画家承认他最佩服的就是毕卡索。但他决不是模仿和照搬。他主张“ 中国学术现代化,外国学术中国化” ,他吸收外来形式,却注入了中国人的情感、神韵,包括造型和线条的运用。可惜像《地之子》这样具有时代博大宏伟精神和深刻内涵、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作品并不多见。
这幅与《地之子》同一时期、同一风格的作品,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生活于苦难中而憧憬着美好未来的中国女性,同样是一重既压抑而又平静的人物感情,因此,当时有人认为他的作品只暴露了社会的黑暗,没有指出光明的希望和对黑暗的反抗。庞薰琹承认这段时期的作品蒙上了“ 一层薄薄的哀伤” 。但是,他说他爱炸弹那种“ 笨与冷的外衣中裹着火热的心” ,因此,那种压抑而沉静的表情,何尝不是一颗会发出光和热量来的“ 炸弹” 呢?庞薰琹经常说他的作品是“ 文学的绘画” ,因此,许多深邃的含涵,不像德国表现主义绘画那样鲜明、强烈,而是需要花时间细细地去“ 读” 和体会的。整个画面使用的绿色色调,即是画家用于暗示生命的活力,和那画面上三位清秀的女性形象所想表现的意念是一致的。(周昭坎撰文)
在庞薰琹的作品中,有几幅以他生活历程中关系重大的几处住处景象为题材所作的风景画,是反映画家真实心情的精心佳作。这幅《白家庄旧居雪景》,有人认为是画家政治上蒙冤后所作的第一幅作品,阴冷、 滞凝、沉重的情调,反映了他被免职后打发到东郊白家庄两间斗室离群鳏居的忧愤、委屈、迷惘的心情。
其实仔细分析这幅画面的情调并非如此。厚重白雪覆盖的新兴城郊,虽然冷清,但一片微弱温暖的阳光映照着新建的住宅,如同同一时期画家在白家庄斗室里画的那些花卉,透露出的是一样的乐观和富有生机。庞薰琹本是一个乐观豁达的艺术家。当他刚搬到白家庄时,固然因为蒙冤、妻子丘堤去世,使他一月间黑发全白,病至垂危。但经一位老中医点化,知医药无效,全靠自我解愁,于是拿起搁置画笔开始画花,心情逐渐开朗,病渐痊癒。1963年,他又与袁韵宜女士结婚,领一女,生活重新有了信心。因此,他那时虽因作为“ 摘帽右派” ,担任教学工作中仍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发生,但心情上总还是乐观的。因此,对于这幅画的解释应是困苦中仍然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冬天过去即是春天。
不管如何解释画家作此画时的心情,这幅画的构图、色彩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幅经典之作。画面上横的和直的线条分割、冷的和暖的色彩对比,既合理而又巧妙,显示了画家的功底和机智。
抗战胜利后,庞薰琹全家自四川返回上海,居住在英租界虹口区,狄思威路,一座三层的楼房。他整日在阁楼中埋头作画。大批唐代白描舞蹈图是在此完成的。这幅油画风景,表现了典型的欧式楼房与前景的中式瓦房,形成有趣的对比,整幅作品淡雅平和,清新隽秀。(庞均文)
这幅画原是一幅水彩,作于四十年代,现由当时的邻居傅雷之子,著名音乐家傅聪保存。1973年,画家按水彩原样复制了这幅画。画家于四十年代在牯岭旧居度过了战争时期动荡而有意义的时光。他在那里深刻地了解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完成了从外国艺术传统中摆脱出来的挣扎,走上了回归和发展民族传统的艺术道路,并为发展中国的工艺美术教学作了有益的铺垫。而与邻居、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亲密相处的友情,更使他难于忘怀,特别是傅雷夫妇于“ 文革” 中的自杀,更使遭到相近劫难,刚从“ 牛棚” 里放出来的庞薰琹勾起了往日的回忆和对挚友的悼念。(周昭坎撰文)
纯写风景的画作在庞薰琹的作品当中,虽然不是占有很重要的比例,但是对画家来说,皆赋有生命中另一层写实的意义。本幅这种以俯瞰的视点来安排场景的饰局,通称为全景画(Panorama)。这样的视点处理,常使透视的层面不仅由近到远,空间亦随之向垂直高低的方向逐渐扩展。仿佛登高峰而望之,视野辽阔,一景一物皆尽收眼底。(林妙玉文)
1938年,庞薰琹深入到“ 地无三里平” 的贵州山区,当地土著居民的歌舞和淳朴的性格、健壮的体格、欢快自立的精神,极大地吸引了他。他踏遍八十多个苗家村寨,用他的画笔创作了二十幅《贵州山民图》。《橘红时节》便是其中的一幅。庞薰琹在创作《贵州山民图》时,选择了一种适合表现个性特征的独特艺术形式,那是中西绘画融合成有机整体的崭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标志着他是在与法国的传统决裂中探索着自己的艺术道路,因而有的批评家称这批作品为“ 他的艺术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 。为此,其中10幅为英国皇家协会收藏,其余则为中国美术馆所珍藏。
从《橘红时节》这幅画上可以看出,画家将画面作了高度平面化和装饰化的处理,写实和变形结合起来,具体的人物形象和非具体的装饰图案结合起来,再现客观对象和表达主观情感结合起来,作品艺术形式和谐完美,从形式美的外表迸发出艺术家心灵深处的激情。同这一时期不少效力于融合中西绘画技巧的画家相比较,庞薰琹无疑走在这支队伍的前列。香港的高美庆博士在《20世纪的中国绘画》一书中如此评论庞薰琹的这批作品:“ 线条的运用与赋予图案性造型,使他这类作品具有一种柔和、优美的魅力和极强的装饰性。……庞薰琹是透过中西艺术合壁,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
诚然,面对开发一种不曾有过的新的审美观念的确立,道路是不平坦的。恰如画家在《自剖》(1943年)一文中所述:“ 我所描写的贵州的同胞,无容讳言,与实际的他们离得很远。不能拿民族学的尺寸来量它。因为笔下总不免流露出自己。可是服饰方面,曾尽量保存它原来面目,因此,给我不少束缚,……” 。
庞薰琹认为,这些装饰图案是苗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是表达他们艺术的一个丰富多彩的方面,是苗族人民生活的一个特色。在他的创作中,苗族装饰艺术和苗族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祇有引用和发展到工艺美术中去的时候,它才是孤立存在的。《盛装》局部,1942年,水彩画,43.5*35公分,中国美术馆藏。不难看出画家对民间图案怀有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贵州山民图》系列画,确实是珍贵的苗族风习与服装的研究资料。《情话》,1943年,水彩,46*19公分,庞薰琹家属藏。在完成《贵州山民图》的同时,庞薰琹还画了一批反映苗民民俗的作品。
《持鎌》,1942年,白描,42*32公分,中国美术馆藏。《归来》,1944年,白描,42*32公分,中国美术馆藏。《走亲》,1943年,白描,42*32公分,庞薰琹美术馆藏。《母与子》,1944年,白描,42*32公分,中国美术馆藏。这些白描作品是庞薰琹的创作素材,而有一些显然又于事后重新画过,本身即似中国古代《绣像》类的创作,四十年代的庞薰琹是白描高手,眼明手巧,走笔如行蛇,游丝似银钩,傅雷称赞他“ 具有东方人特有的气质,他的线条艺术成就很高,是东方人中的佼佼者” 。(周昭坎撰文)
在庞薰琹的作品里,静物的作品(不包括花卉)并不多见。这幅于四十一岁时作于广州的《静物》,构图、造型和色彩都很严谨。
对于庞薰琹来说,“ 严谨” 的含义决不是毕恭毕敬地自然主义地描绘对象。一如他的一贯作风,他在描绘对象时,写实和写意、绘画性和装饰性巧妙地揉和在一起,而在这一幅作品中,更让人觉得“ 天衣无缝” 。
譬如画面上的石膏头像和梨是写实的,而陶罐的背景上的壁毯都是装饰性的画法,二者既是对比的,又是谐和的,显然深沉而丰富的色彩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而所有的色彩又突出了梨的黄嫩,使整个画面产生亮暗轻重多层次的效果,情趣横生。
庞薰琹一直热衷于图案画。他借用这幅静物“ 写生” ,在壁毯和陶罐上尽情地表达了他对图案的热情,刻划得十分仔细认真。这也许与他当时正在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开设工艺美术课不无关系,他希望学生在学习绘画基础课程的时候,就开始对图案设计产生兴趣。因此,这幅作品极可能是当时的示范作品。
无所不在的装饰情趣
庞薰琹在1957年于“ 反右” 的声浪中,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有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几乎停止艺术的创作,而这段真空期也使他与早期前卫的艺术之路造成断层。其后的有生之年只专注于小幅花卉的描写,而不论艺术界的风云。尽管如此,此间他在装饰画方面投注精力,费时二十年始编纂而成的《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对中国文化仍是一项不可抹灭的贡献。本专栏所摘选的画作局部,即可显示出庞氏在创作上对装饰绘画的一贯性。其实在早期之同质性的淡彩与线描勾勒的画作中,如《盛装》及《带舞》系列,无不洋溢着装饰情调。颜色轻俏活泼,线条细緻柔美,有融合装饰与绘画为一体的意图。其装饰意味和创作结合中国传统特殊的人文之美,展现的不仅是艺术创造的功力,亦附有设计上实用的价值。(林妙玉撰文)
1931年庞薰琹与志同道合的朋友酝酿成立“ 决澜社” ;1932年9月中旬庞薰琹在上海开他个人的第一次画展,在此次画展中认识丘堤,而丘堤也因为庞的关系,加入了决澜社,成为决澜社当时唯一的女会员,后来又有女会员加入。1932年10月中旬,丘堤以一幅花卉作品参加决澜社第一次画展,并且得奖。此幅《静物》是第二次参加决澜社画展的作品。庞薰琹与丘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相知相惜而结成连理。(庞均撰文)
《背篓》,1946年,水彩画,46*30公分,中国美术馆藏。
继于四十年代初完成二十幅《贵州山民图》之后,庞薰琹于1946年回到上海,又以同样的手法,以苏南农民为对象,创作了水彩画《背篓》、《小憩》、《捉鱼》、《割稻》等作品。《背篓》是其中最精彩的一幅。
这幅作品,造型的真实和写意结合,形意兼备。
和画贵州苗民的服饰一样,画家刻意细致地描绘了印花布衫的图案,但与苗民图不同的是,这种刻意的描绘也用于背篓的编紮和作为背景的树叶的描绘,因此,少了原先那种生硬拼贴的感觉,从而成为一幅完整的、富有装饰趣味的作品。
同时,于人物神情的刻划,庞薰琹也下了更大的功夫,温柔、内秀的气质和健美、勤劳的外在体形结合,塑造了完美的东方女性形象,尤其是眉宇间含蓄的表情描写,很有些东方蒙娜丽莎的意味,十分耐人咀嚼。
如果达文西通过蒙娜丽莎永恒的微笑的描写,以预示人文主义精神的胜利,那么,庞薰琹显然企图以一位劳动妇女脸上同样表情的描写,召唤着新时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到来。当时,有的批评家批评他不顾社会黑暗面而片面描写光明,导人盲目乐观。庞薰琹即予反驳:“ 我为什么不常写社会的阴暗面,因为现在我以为写黑暗不如写光明;人生需要艺术,艺术能给人以鼓励……反之,过去我的作品时时蒙上一层薄薄的悲哀。” 显然,这是他经过人生体验后选择的创作道路。(周昭坎撰文)
庞薰琹曾哀叹他在蒙难期间想画人而没有人敢让他画。但是,1962年,他的学生罗真如(现在也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主动为他做模特儿。这是他许多年没画人像以后画的第一张人像。这张人像的画法和他十六年前画的《背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幅画后来又由画家复制了一幅送给罗真如。和他创作苗民图时一样,他像“ 绣花” 一般把蓝花布的纹样照原样画出。由于画面上其他道具作了同样精细的处理,整个画面大为统一和谐,别具一种装饰意味的情趣。(周昭坎撰文)
多明尼克·吉尔兰戴欧(Domenico Ghirlandaio)《女人像》,1488年,蛋彩。此幅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不论在姿势的调动以及人物神情的刻划上,都出现了极其相似的安排,而其衣饰的雕琢讲究,也是非常细緻的工笔手法。此种採人物侧身的构图方式,避开对象与观者直接视觉接触所产生的不安,而使画中人与观者双方都较能以第三者的立场参与整个画面所蔓延的氛围。(林妙玉撰文)。
庞薰琹此系列的创作于重庆展出时颇引出一番争议,有人批评他画“ 美人儿” 或“ 唯美主义” ,更有人贬为“ 多少带些低能的趣味主义的东西。” 但庞薰琹在《自剖》中反驳道:“ 十多年前读邓肯的自传,看惠格曼的表演,又曾数次仔细参观印度尼奥太·依奥迦的舞蹈,自那时起在我胸中时时起伏种种幻象。我曾有过这样痴愿,想研究已绝亡的汉族的‘舞’,可惜环境、时间、精神,都不允许我实行我的理想。近年来,我的兴趣又转到古代的图案,连带对于服饰也发生了兴趣,……所以,我用手边有限得很的资料,凭我的想像作此舞装。……现在赶快去研究还来得及找到一点贫乏的参考,不然连一点贫乏的参考,也会被时间消灭了的。为保存中国的文化著想,不见得是无所谓吧!” 现在看来,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民族危亡关头,一些人对艺术家提出苛刻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学者的庞薰琹想的是做学问,不免显出十足的书生气,因此,他的这组作品不免不合时宜。而于半个世纪后再看这些创作,诚如英国美术史论家苏立文于《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一书中所述:“ 他的精神系列画‘舞蹈者’,渊源于他对唐代艺术与服饰的研究,也同样引人入胜。这些作品尽管使用的是中国画笔,在其理想化的加工中,透露出对西方艺术的熟稔。” 确实,从这组作品里,我们感受到了盛唐风范,却也觉察到了那个时代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而在表现技法上还可以隐约觉察日本浮世绘的趣味,而当庞薰琹还在巴黎的时候,欧洲现代画派大师们正对日本浮世绘崇拜得五体投地,苏立文所指的“ 西方艺术的熟稔” 也许指的就是这一点,不少欧洲现代派画家都临摹过浮世绘。
尽管对这组画的舆论褒贬不一,不过庞薰琹却斩钉截铁地声明:“ 似乎因为我画这些唐装,有人就说我画‘美人儿’。这新的‘头衔’,我祇能拒谢。我不单不是唯美主义者,而且我也反对唯美论。这类作品我第一次试作,但也将成为这类作品的最后一次试作。” 不过,1946年,傅雷为他举行第六次个人展览时,非常佩服他的“ 铁线” 钩勒技巧,所以一再希望他能展出这些作品,因此他复制了几幅带彩的。这一幅就是其中之一。1983年,这些作品又一次在纪念他执教五十二周年时于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庞薰琹画展》中展出。
这铁线白描确实是第一流的。庞薰琹的经验之谈是:画白描不能允许一点干扰。情绪不稳定不要画。一开始画应该画到完成,中间吃饭或休息一会也不行。墨水要足那画一幅的,中间加水不行。画人脸从右眼靠鼻梁处动笔,用笔要轻秀,中间隆起。靠眼珠处,用笔手底要加力,这种眼睛可以加深强度。收笔要轻,不留笔痕。更难的是画左眼,从右到左是反手。画了双眼,接着画双眉、鼻、嘴,最难的是人脸轮廓,从额际一直画到头部,一笔画成,用笔要稳又有变化。以上五幅白描作品为庞薰琹的带舞系列,分别是《带舞》之一、之三、之四、之八及之十二。于1942年 ̄1945年间作于成都。尺寸一律33*44公分,为中国美术馆所收藏。(周昭坎撰文)
这幅画记录的也是画家于四十年代在四川郫县的旧居,但这是一幅构图和色彩奇巧的佳作。
庞薰琹一再说过:“ ……如果,我的作品能使你感到一点美感,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他确实如此对待他的每幅作品。在平凡中发现美,然而加以表现,把美奉献给人们。
在这幅画的画面上,一片小小的竹林,一幢平常的木屋,经他妙手经营,给人无比温馨。他巧妙地将21根竹枝、10根树杆和10根房柱,用5根椽梁和一排窗户加以分割,应用的仍然是他所熟稔的现代构成分割的原理,但那么自然、机巧。无怪乎,有位批评家评述他的作品:有古典主义的和谐、完整、庄重与肃穆;有浪漫主义的诗情;有写实主义的诚实;有表现主义的虚灵;有印象主义的率真;有一切形式主义的智巧。就在这么一幅小小的风景画里,我们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竹林的宁静。画家就在这幢房子里整理着他收集来的许许多多古代纹样,设计着中国工艺美术的未来。这幅画现在由画家的亲属收藏于上海的家中。
庞薰琹一生不断改变自己的画风,他觉得用一种画法老画一种题材是最没有意思的。因此,他在灌县写生时画的一组风景,就是别样风味。构图采取了中国画高视点、散点透视的经营方法,并且运用了中国画的线条和皴法,只是用了西洋画的工具和材料,较之中国画更强调色彩的作用而已。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的行动得到了自由,经常离开北京去外地考察、讲学、写生。一路上他用中西画法画了不少风景。这是其中一幅油画。(周昭坎文)
据庞薰琹的女儿、女画家庞涛回忆:“ 父亲不画花。因为妈妈专门画花,他认为他不如妈妈画得好。”
但自前妻丘堤女士去世后,他开始画花,而且画了很多花。画得很有心意。庞薰琹自述:“ 是不是我爱画小油画?不是。因为我的房间里,找不出比两米大的空地。是不是我爱画花?也不是。我想画人,谁敢理睬我让我画?……祇有花,有些好心人採些野花送我,我还在垃圾箱中捡些人家不要的花,我把倒头烂叶的花画得美些……” 这是蒙难的庞薰琹在苦难日子里的辛酸回忆。显而易见的,那时他画花,既是无奈,却也是精神的寄托。
他画花,不是简单的模写对象,而是根据画面需要构图变化,既依据对象,又不完全依据对象,而任凭自己的意图经营画面。他不无意地对人说:“ 有时别人送我一枝很好看的花,我就不断变换这枝花的放置位置,可以画出一簇好看的花来” ,他就是这样在苦难中找“ 乐” ,忘却了自己,把大自然赋予的一丁点美,一丁点生气,放大,升华,再现于画面,既是他高尚、乐观的情操体现,也是他于绘画艺术的奉献。
这幅《美人蕉》是他这一类花卉作品的一个典型。不难看出,整个画面(包括背景)是画家“ 设计” 的结果,花、叶陈列有致,色彩对比靓丽,富有强烈的装饰趣味。
这幅同样具有设计意味的装饰性花卉作品,在使用西洋画工具时,却运用了中国工笔花卉的精细线条,蓝灰色彩基调,衬托出了白色玉兰的温馨和生气,给人以愉悦的快感。
庞薰琹总是不停地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作画。这幅作品与《玉兰花瓶插》为同年的作品,虽然构图同具设计意味的匠心,但用色用笔就不那么细腻,而只是在绿色基调中寻找差别而显现描写对象的品格、气质。(周昭坎文)
一大把盛开的花朵插在一只宋瓷花瓶里,形式和谐完美的画面充满了装饰的美。整个画面作高调处理,色彩鲜明,构图饱满,显示出蓬蓬勃勃的生命力量。很难想像这样一幅充满生命活力的作品,却是一位不久前刚从“ 牛棚” 里放出来,还背着沉重的政治冤屈未获平反的老艺术家的手笔。
王安石曾有这样的诗句:“ 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何缘身处逆境的庞薰琹却能用自己的画笔把春色凝固于画面而永驻人间?他的一首题为《小草》的自喻诗,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注释:“ 一颗平平常常的小草,虽然饱经烈日秋风、旱涝雨雪,毕竟不可摧折,春风吹又生,始终顽强如故;甚至即使连地下的老根也枯死了,可是在死去的老根旁,却又长出新根长出了新芽,草地仍是一片绿色……”
永远乐观的信心,永不疲倦的探索,使老人永葆艺术的青春!他从不使自己笔下的花带有伤感,不论是浓彩艳丽的鸡冠花,还是淡雅飘逸的水仙花,都给人以具有生命力的美感。
诚然,庞薰琹的画花,除了寄情、言志之外,更热衷于艺术的探索。从这幅画里,我们看到画家感兴趣的不仅是关于装饰性的设计意匠,更对色彩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
他在这幅画中,可以说把对象的固有色的色相强调到极顶,全然不顾所谓环境色的制约。他认为:“ 色彩有巨大的作用” 。“ 一切器物如不加上点色彩,那么生活一定变得枯燥。” 过去士大夫阶级认为浓色不如淡色雅,淡色不如墨色高。几百年来受著这种理论的影响,使美术工作者在色彩的表现力上比较弱,在色彩的感觉上也比较迟钝。“ 不重视色彩的研究,这是非常错误的。” 他力图通过器物固有色的描绘,来提高画家对色彩的敏感和表现力。他在这幅画中,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人们:对比的固有色,可以在同一画面上取得和谐的美。而他对白色瓷瓶在高调画面上的描绘,更显示了他表现固有色的高超本领。
庞薰琹晚年画了不少水墨画。当他用强调“ 墨分五色” 的中国传统笔墨画花时,他仍然十分强调表现花的固有色。也许他认为花之所以美,正应当是它们艳丽的固有色。(周昭坎文)
丘堤《向日葵》,1947年,油画,61*50公分,庞均私人收藏。此幅作品画于1947年广州光孝寺广东艺专,丘堤与庞薰琹同时画一组向日葵静物,事后庞薰琹自认为作品没有其妻画的生动,他的那一幅画作就深藏不露了。直至近日才被发现。丘堤用笔有力、朴实、色彩绚丽。(庞均文)
庞薰琹好象很喜欢画鸡冠花,在他的作品中有好几张鸡冠花,情趣各异。有的绘画性强,有的装饰性强,有的严谨、有的洒脱。这张作于1983年的作品,把鸡冠花和吊兰画在一起,用笔轻松活泼,色彩浓艳强烈,充满活力,很难令人相信出自一位七十七岁老翁之手,这也许和他政治上得到平反、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庞薰琹的梦又获得重新编织的机会,心境愉快有关。但人们没有预料到他两年后就匆匆离开了人间,因此,有位美术评论家认为:如果庞薰琹能继续活下去,他在绘画方面将恢复年轻时代的活力,作为曾是三十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领头人,他必将在八十年代的青年美术新潮运动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使青年美术家少走不少弯路。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笔者认为庞薰琹如果活着,未必会和“ 85新潮美术” 的那些青年走在一起,正如与他同时代的洪毅然在纪念庞薰琹的文章《探索者的足迹》一文所述:“ 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实乃远远不自今日始。不过,我们那时的‘现代’概念,其内涵却与当今某些误解‘现代化’即全盘‘西方化’的人们之‘现代’概念,并不相同。我们虽然也不排除适当吸收西方艺术(包括其‘现代派’艺术)某些于我可用之形式和技法,却仍始终坚持贯彻‘中国学术现代化,外国学术中国化’之原则,既不顽固保守,复古倒退,也不亦步亦趋紧跟洋人爬行。” 老一辈的道路早已经过自己的实验而选定,而青年人是一定要亲自把西方现代绘画一百年走过的路再走一遍才会认定自己该走的路,尤其是因为大陆与外部世界封闭了四十年,庞薰琹又经过如此坎坷,青年人未必会听从他的劝导。有趣的是,洪毅然在同文中记述了庞薰琹二十年代初到巴黎,也曾于夜间,把两眼闭起来涂抹,借求意外的‘现代’效果。而当今一些青年人还把寻求‘潜意识’的灵感,当成时髦的新玩意!
此作与1983年所作鸡冠花风格完全不同。浑厚凝重,颜色用得很厚,用笔粗狂有力,构图饱满充实。
这张作品的写意风格,和《鸡冠花与吊兰》有相似之处,潇洒轻松,完全摆脱了描摹对象的拘泥,如不经意地“ 玩弄” 笔触和色彩,恰到好处地表现了生命的跃动和画家的抒情。(周昭坎文)。
(载台湾《中国巨匠美术周刊》中国系列第127期,总第227期199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