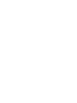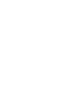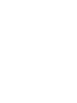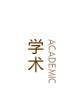渊源有自·诗画合融——传统主义的恪守
2013-03-28 01:48:00来源:常熟美术馆点击:4091
作 者:夏淳
出 版 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3月第1版
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有着两条十分清晰的路径,一是中西融合,二是传统演进。长久以来,中国美术界对这两条路径的定性截然不同。在“ 西方” 等同于“ 现代” ,“ 中国” 等同于“ 传统” 的思维模式下,具有开拓精神的“ 中西融合” 被认为是明智的中国画现代转型之路;而“ 传统演进” 则被认为还未进入现代范畴,故常被看做“ 保守型” 。然而,随着近年来,美术界对20世纪中国美术所进行的反思性研究,“ 传统主义” 、“ 融合主义” 、“ 大众主义” 和“ 西方主义” 同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基本形态,而以“ 自觉” 为标志的各种主张、方案成为判断这个时期中国美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当我们在这里阅读、欣赏、品评钱持云的山水画艺术时,便有了可贵的理论标识。
钱持云的山水画艺术选择了传统演进的道路,这从内在的,艺道层面的维度来看,体现了先生对传统审美功能的强调,对价值理念中国优位式的陈述和对中国画自律性演进的自信与自觉。这种认识同时也表现为对“ 何为中国画主线” 传统内核的体知。持云先生对自己的艺宗曾有这样的叙述“ 董巨始凿鸿濛天” 、“ 南宗开画派,衣钵有巨然” 、“ 辋川腾气韵,洪谷隐深渊” 、“ 大痴妙迹天下传,解索披麻画百川。愿借先生一滴水,写尽秋山万叠泉。” (钱持云《三素草堂杂咏百首》),这些表明了他对董其昌所谓“ 南宗” 脉络的认同。沿袭着“ 南宗” 学说的理路,他对这条“ 主线” 上还应该包括的“ 四王” 、“ 四僧” 以及近现代的传统派大家都有过深入细致的研习。《黄鹤山樵笔意》、《痴翁遗格》、《仿八大山人法》、《仿石涛山水》、《拟各家山水册》等作品是持云先生师法古人最直接的表现。先生对古人的执着从表面上看似乎带有一种儒味的“ 隐” ,但当我们仔细品味过他的作品以后,便能知道他对中国画气、意、韵美学和笔墨以及“ 诗画一律” 的修养认同,正是这些保持了中国画的纯粹性。
从外向的,时世层面的维度来看,传统演进无可避免的将会面对巨大的社会现实和复杂的时代语境,但这其中“ 演进” 并不是以是否融合了西方、现代的思想意识为判断标准,而应被看做画家对现代情境的“ 自觉”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陈师曾、黄宾虹、潘天寿等“ 传统主义” 大家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支持多元文化观念的另一种“ 现代” 。常熟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绘画上黄公望、王翚、吴历等画家的卓越成就,让后人更为容易的便能找到效仿的对象。尤其以王翚为代表的虞山画派,一直以来崇古拟古之风未断,这直接影响到了后世的很多画家,持云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先生认为艺术上的折中主义态度并不可取,对传统中精思奥义的传承更为重要,虽经时代变迁“ 未可以或废” 。在先生看来,师法古人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 钻进去” ,并在其中“ 翻上几百个筋斗” ,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持云先生对中国画的创新始终抱着相对谨慎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 不管是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总要发挥中国画的特点,保持中国的民族特色。” 很显然,正是出于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和对中国画既定形态的维护,使得持云先生在中国画内在理路遭遇现代转型之时,自觉得把对传统经典语言的回溯与历练,作为首要的问题来考虑。
持云先生所追随的文人画理路,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书法化和诗化。书法化体现为外在的、视觉的笔墨要求。先生自幼随父习草,在这样的家训之下,得一笔挺秀,这直接影响到他绘画中的笔墨表现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书法入画” 成就了先生正统高雅的笔墨特色。在他的画中,笔迹一如书法,时常从一画开始便紧密相连,以用笔的书写性和运笔的时序性来保证气息的流畅,达到连绵相属,气脉不断。持云先生的用笔,轻快、洒脱、灵动且不板、不刻、不结,刚柔相济又枯而能润,而他的用墨酣而不肥,湿而不腻,并极为注重墨色的多元对比,不同墨色之间大小形状、虚实浓淡的对比;排列组合所构成的不同明度的对比以及墨与纸素之间的黑白对比。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曰:“ 山水墨法,淡则浓托,浓则淡消,乃得生气” ,而持云先生则更为细腻的概述了用墨的妙理,他说:“ 淡从浓处来,浓是淡中得,虽淡犹如深,但浓不觉黑。浓淡本相生,却又复相克,远近何溟迷,高低亦奇特。阴阳转相因,变化无穷极,由来妙画工,墨可分五色” (钱持云《三素草堂杂咏百首》)。正是这种对传统笔墨的熟稔驾驭和深刻理解,最终让我们在他的画中看到了董源的“ 平淡天真” ,黄子久的“ 气清质实” ,王麓台的“ 简淡古秀” ,石涛的“ 宏博奇异” 和黄宾虹的“ 黑密厚重” 。沙曼翁先生曾形容他的画“ 广取博收,笔笔能见出处” ,并以“ 化境” 称赞其有高古韵味。持云先生把前人的笔墨精神融会至极,真正做到了法古而不泥,求变而不怪,逸笔草草,以笔论气,以墨论韵。
然而,笔墨说到底还只是一种语言,任何技巧与风格都必须屈从观念的境界。先生在承接古人精笔妙墨的同时,更把“ 拟古” 作为通向内心的精神训练,最终建立与古人类似的道德修养和思维范式。这种见贤思齐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对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回避,和对诗化意境的追求。郭熙《林泉高致》曰:“ 尝所诵道古人清篇秀句,有发于佳思,而可成画” ,宋徽宗则题诗《腊梅山禽图》,题画诗自此入元而始盛。持云先生也时常爱取古人佳句,拈其诗意以为画。在《王摩诘诗意图》、《早发白帝城诗意》、《大林寺桃花》等作品中,他通过自身的审美感悟,展开艺术构思,以意、景结合的方式生动再现了古人淡静悠远、朦胧含蓄的诗词意蕴。先生更善以画题诗,并把诗与画的结合视为自身艺术中最重要的元素,以此来明确自己恪守传统的理据。他曾说:“ 常熟在明清时期有虞山诗派,影响甚大,而吴历、蒋廷锡等画家皆善诗,自己虽略有诗词基础,自应温故知新地继续钻研。” 正是秉持着这种恭谦的态度,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先生便常与曹仲道等诗家前辈在虞山脚下谈诗论史,分韵作诗,群相步和。在先生的巨幅山水画作品《清奇古怪图》中,他以邓尉司徒庙中四株遭雷电轰劈的古柏为创作蓝本,通过苍劲有力的笔法刻画出古柏虽因天灾而残损,盘根错节却依旧雄健有力的不凡气势,又题以“ 千年古柏自撑持,雷劈霜欺犹蔓滋。铁骨铮铮天下士,从教神物作良师” 的七绝,将古柏的坚忍不拔人格化,隐喻出文人士大夫刚正不阿、坚强不屈的高尚气节。“ 山不见图经,水无有典录。碧水自在流,春山随意绿” ,这是他在《碧水春山图》上题写的诗句。综观整幅作品,葱郁蓬勃、虚淡悠远,给人以清净质朴的感觉。吟诗寻思,又让人感慨自然界万物生机盎然和人生、生命的流光易逝。持云先生以画喻意,以诗点画,在人与山水的情绪交融中,把超越世俗的情感归于自然,最终让人想要把自身也安顿在其中。
数百年来中国画家之所以爱山水、画山水,乃假借山水之形把抑郁在生命内部的感情扩展向纯洁的自然中去,画家沉淀了自我的一切思虑之后将自然精神化,自然风景便因为心灵的投射有了精神,这便是传统中国画将审美情感自觉内化的表现。而中国古代诗歌因认识到抽象符号的语言与前概念的情感之间不能建立直接的联系,从而选择了一条“ 壮景抒情,借物言志” 的发展道路。于是主体情感的表达便成为诗画得以相融的本质所在。持云先生深知这其中的妙理,在他看来,“ 画中意” 和“ 诗中情” 一样,有赖于意象的获得。诗由感而见,便是诗中有画;画由见而感,便是画中有诗。但单纯的依靠写生得到的零散经验和形色意味并不能完全实现“ 画是有形诗” 的美学要求,以诗情入画,就必须使绘画创作超越形似。对持云先生来说,用以审视的“ 目” ,固然不可忽视;用以感受的“ 心” 则更具决定意义。“ 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 。(符载《观张员外画松石序》),这里所强调的主观情思对现实的熔铸和再造与固定的自然物理形态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文人画讲究悟对通神,迁想妙得,依靠传统范本中所提示的笔墨、程式和观看方法已经可以为己所用。“ 师造化” 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弱化的,诗化的情感表现与精神追求,关键还在于画家深邃的内心。我想这也许正是持云先生把“ 师心、师古、师真髓” 视作自己精神碑记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他的山水画最终回归到“ 诗魂书骨” 的文人画精髓之中。
在我们思考与探究钱持云的中国画艺术时,并没有花费太多笔墨去回溯他的人生经历和从艺之路,但我们依旧不该遗忘这样的事实: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像钱持云这样的画家,无论其作品表示出了多少承接传统的特质,他究竟与历史上那些不朽名作有过何种方式的交汇;在常熟工艺美术厂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工艺美术的产业化对他的画风产生过怎么样的影响;他更早前所从事的国文教学工作,是否可以被看作成就其诗词造诣的重要原因。我想,这些都应该成为风格学探究的合理因素,只不过就作品本身而言,我们仍然可以用更为理想化的语汇加以讨论。
无论如何,今天当我们把传统主义放入中国继发现代性的框架中进行讨论时,应该看到,它是以现代生存情境为根基,以西方为潜在参照系而凸显中国本土和传统的策略行为,传统主义也是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中最具有原创性的部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画越是现代化,现实的需求就越是会对传统的信条、原则和规范作出名存实亡的阐释,越是用文化进化主义的纵向规定去取代文化相对主义的横向规定,越是为中国画概念本身增加否定性,也就越是背离中国画固有的既定形态。站在这样的立场之上,恪守传统就变得极为睿智与必要,也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之上,钱持云先生的山水画艺术为中国画传统转型的内涵和文化多元现代性提供了最为有效的例证。
出 版 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3月第1版
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有着两条十分清晰的路径,一是中西融合,二是传统演进。长久以来,中国美术界对这两条路径的定性截然不同。在“ 西方” 等同于“ 现代” ,“ 中国” 等同于“ 传统” 的思维模式下,具有开拓精神的“ 中西融合” 被认为是明智的中国画现代转型之路;而“ 传统演进” 则被认为还未进入现代范畴,故常被看做“ 保守型” 。然而,随着近年来,美术界对20世纪中国美术所进行的反思性研究,“ 传统主义” 、“ 融合主义” 、“ 大众主义” 和“ 西方主义” 同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基本形态,而以“ 自觉” 为标志的各种主张、方案成为判断这个时期中国美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当我们在这里阅读、欣赏、品评钱持云的山水画艺术时,便有了可贵的理论标识。
钱持云的山水画艺术选择了传统演进的道路,这从内在的,艺道层面的维度来看,体现了先生对传统审美功能的强调,对价值理念中国优位式的陈述和对中国画自律性演进的自信与自觉。这种认识同时也表现为对“ 何为中国画主线” 传统内核的体知。持云先生对自己的艺宗曾有这样的叙述“ 董巨始凿鸿濛天” 、“ 南宗开画派,衣钵有巨然” 、“ 辋川腾气韵,洪谷隐深渊” 、“ 大痴妙迹天下传,解索披麻画百川。愿借先生一滴水,写尽秋山万叠泉。” (钱持云《三素草堂杂咏百首》),这些表明了他对董其昌所谓“ 南宗” 脉络的认同。沿袭着“ 南宗” 学说的理路,他对这条“ 主线” 上还应该包括的“ 四王” 、“ 四僧” 以及近现代的传统派大家都有过深入细致的研习。《黄鹤山樵笔意》、《痴翁遗格》、《仿八大山人法》、《仿石涛山水》、《拟各家山水册》等作品是持云先生师法古人最直接的表现。先生对古人的执着从表面上看似乎带有一种儒味的“ 隐” ,但当我们仔细品味过他的作品以后,便能知道他对中国画气、意、韵美学和笔墨以及“ 诗画一律” 的修养认同,正是这些保持了中国画的纯粹性。
从外向的,时世层面的维度来看,传统演进无可避免的将会面对巨大的社会现实和复杂的时代语境,但这其中“ 演进” 并不是以是否融合了西方、现代的思想意识为判断标准,而应被看做画家对现代情境的“ 自觉”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陈师曾、黄宾虹、潘天寿等“ 传统主义” 大家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支持多元文化观念的另一种“ 现代” 。常熟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绘画上黄公望、王翚、吴历等画家的卓越成就,让后人更为容易的便能找到效仿的对象。尤其以王翚为代表的虞山画派,一直以来崇古拟古之风未断,这直接影响到了后世的很多画家,持云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先生认为艺术上的折中主义态度并不可取,对传统中精思奥义的传承更为重要,虽经时代变迁“ 未可以或废” 。在先生看来,师法古人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 钻进去” ,并在其中“ 翻上几百个筋斗” ,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持云先生对中国画的创新始终抱着相对谨慎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 不管是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总要发挥中国画的特点,保持中国的民族特色。” 很显然,正是出于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和对中国画既定形态的维护,使得持云先生在中国画内在理路遭遇现代转型之时,自觉得把对传统经典语言的回溯与历练,作为首要的问题来考虑。
持云先生所追随的文人画理路,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书法化和诗化。书法化体现为外在的、视觉的笔墨要求。先生自幼随父习草,在这样的家训之下,得一笔挺秀,这直接影响到他绘画中的笔墨表现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书法入画” 成就了先生正统高雅的笔墨特色。在他的画中,笔迹一如书法,时常从一画开始便紧密相连,以用笔的书写性和运笔的时序性来保证气息的流畅,达到连绵相属,气脉不断。持云先生的用笔,轻快、洒脱、灵动且不板、不刻、不结,刚柔相济又枯而能润,而他的用墨酣而不肥,湿而不腻,并极为注重墨色的多元对比,不同墨色之间大小形状、虚实浓淡的对比;排列组合所构成的不同明度的对比以及墨与纸素之间的黑白对比。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曰:“ 山水墨法,淡则浓托,浓则淡消,乃得生气” ,而持云先生则更为细腻的概述了用墨的妙理,他说:“ 淡从浓处来,浓是淡中得,虽淡犹如深,但浓不觉黑。浓淡本相生,却又复相克,远近何溟迷,高低亦奇特。阴阳转相因,变化无穷极,由来妙画工,墨可分五色” (钱持云《三素草堂杂咏百首》)。正是这种对传统笔墨的熟稔驾驭和深刻理解,最终让我们在他的画中看到了董源的“ 平淡天真” ,黄子久的“ 气清质实” ,王麓台的“ 简淡古秀” ,石涛的“ 宏博奇异” 和黄宾虹的“ 黑密厚重” 。沙曼翁先生曾形容他的画“ 广取博收,笔笔能见出处” ,并以“ 化境” 称赞其有高古韵味。持云先生把前人的笔墨精神融会至极,真正做到了法古而不泥,求变而不怪,逸笔草草,以笔论气,以墨论韵。
然而,笔墨说到底还只是一种语言,任何技巧与风格都必须屈从观念的境界。先生在承接古人精笔妙墨的同时,更把“ 拟古” 作为通向内心的精神训练,最终建立与古人类似的道德修养和思维范式。这种见贤思齐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对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回避,和对诗化意境的追求。郭熙《林泉高致》曰:“ 尝所诵道古人清篇秀句,有发于佳思,而可成画” ,宋徽宗则题诗《腊梅山禽图》,题画诗自此入元而始盛。持云先生也时常爱取古人佳句,拈其诗意以为画。在《王摩诘诗意图》、《早发白帝城诗意》、《大林寺桃花》等作品中,他通过自身的审美感悟,展开艺术构思,以意、景结合的方式生动再现了古人淡静悠远、朦胧含蓄的诗词意蕴。先生更善以画题诗,并把诗与画的结合视为自身艺术中最重要的元素,以此来明确自己恪守传统的理据。他曾说:“ 常熟在明清时期有虞山诗派,影响甚大,而吴历、蒋廷锡等画家皆善诗,自己虽略有诗词基础,自应温故知新地继续钻研。” 正是秉持着这种恭谦的态度,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先生便常与曹仲道等诗家前辈在虞山脚下谈诗论史,分韵作诗,群相步和。在先生的巨幅山水画作品《清奇古怪图》中,他以邓尉司徒庙中四株遭雷电轰劈的古柏为创作蓝本,通过苍劲有力的笔法刻画出古柏虽因天灾而残损,盘根错节却依旧雄健有力的不凡气势,又题以“ 千年古柏自撑持,雷劈霜欺犹蔓滋。铁骨铮铮天下士,从教神物作良师” 的七绝,将古柏的坚忍不拔人格化,隐喻出文人士大夫刚正不阿、坚强不屈的高尚气节。“ 山不见图经,水无有典录。碧水自在流,春山随意绿” ,这是他在《碧水春山图》上题写的诗句。综观整幅作品,葱郁蓬勃、虚淡悠远,给人以清净质朴的感觉。吟诗寻思,又让人感慨自然界万物生机盎然和人生、生命的流光易逝。持云先生以画喻意,以诗点画,在人与山水的情绪交融中,把超越世俗的情感归于自然,最终让人想要把自身也安顿在其中。
数百年来中国画家之所以爱山水、画山水,乃假借山水之形把抑郁在生命内部的感情扩展向纯洁的自然中去,画家沉淀了自我的一切思虑之后将自然精神化,自然风景便因为心灵的投射有了精神,这便是传统中国画将审美情感自觉内化的表现。而中国古代诗歌因认识到抽象符号的语言与前概念的情感之间不能建立直接的联系,从而选择了一条“ 壮景抒情,借物言志” 的发展道路。于是主体情感的表达便成为诗画得以相融的本质所在。持云先生深知这其中的妙理,在他看来,“ 画中意” 和“ 诗中情” 一样,有赖于意象的获得。诗由感而见,便是诗中有画;画由见而感,便是画中有诗。但单纯的依靠写生得到的零散经验和形色意味并不能完全实现“ 画是有形诗” 的美学要求,以诗情入画,就必须使绘画创作超越形似。对持云先生来说,用以审视的“ 目” ,固然不可忽视;用以感受的“ 心” 则更具决定意义。“ 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 。(符载《观张员外画松石序》),这里所强调的主观情思对现实的熔铸和再造与固定的自然物理形态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文人画讲究悟对通神,迁想妙得,依靠传统范本中所提示的笔墨、程式和观看方法已经可以为己所用。“ 师造化” 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弱化的,诗化的情感表现与精神追求,关键还在于画家深邃的内心。我想这也许正是持云先生把“ 师心、师古、师真髓” 视作自己精神碑记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他的山水画最终回归到“ 诗魂书骨” 的文人画精髓之中。
在我们思考与探究钱持云的中国画艺术时,并没有花费太多笔墨去回溯他的人生经历和从艺之路,但我们依旧不该遗忘这样的事实: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像钱持云这样的画家,无论其作品表示出了多少承接传统的特质,他究竟与历史上那些不朽名作有过何种方式的交汇;在常熟工艺美术厂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工艺美术的产业化对他的画风产生过怎么样的影响;他更早前所从事的国文教学工作,是否可以被看作成就其诗词造诣的重要原因。我想,这些都应该成为风格学探究的合理因素,只不过就作品本身而言,我们仍然可以用更为理想化的语汇加以讨论。
无论如何,今天当我们把传统主义放入中国继发现代性的框架中进行讨论时,应该看到,它是以现代生存情境为根基,以西方为潜在参照系而凸显中国本土和传统的策略行为,传统主义也是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中最具有原创性的部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画越是现代化,现实的需求就越是会对传统的信条、原则和规范作出名存实亡的阐释,越是用文化进化主义的纵向规定去取代文化相对主义的横向规定,越是为中国画概念本身增加否定性,也就越是背离中国画固有的既定形态。站在这样的立场之上,恪守传统就变得极为睿智与必要,也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之上,钱持云先生的山水画艺术为中国画传统转型的内涵和文化多元现代性提供了最为有效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