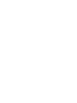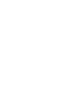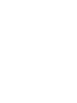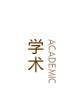不再道别的重写——在离开黄公望的日子里
2014-08-28 01:47:00来源:常熟美术馆点击:5147
作 者:卢 缓(中华艺术宫学术部副主任、策展人,艺术史学博士)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黄公望,一位成就了中国文人山水画成熟样式的代表艺术家,一位以艺术修养实现其作品“ 技进乎道” 的典型人物,一位被尊为“ 元四家” 之首,尤其被董其昌等后世推崇为“ 南宗” 的大师。于是,黄公望艺术便成为了中国文人绘画的代名词,又经历了几百年的摹学与演绎而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趣味。
值此,离开黄公望已660周年,今天我们再一次仰望大师,或许无有那种离开般的诗意和伤感,却是一种因为追忆形成的反思,一种对黄公望引发的半个多千年的艺术史演变过程的重读、重游与重写。
黄公望对后世的山水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从明代中期到清一代造就了主流的审美取向和历史文化语境。在其后层层累积的中国艺术史上,他作为一位具有开拓意义的里程碑人物,身后追随者的脚步不绝如缕。直至二十世纪初叶,伴随着国运日窘,中国绘画的历史境遇也随着时运流转而变得风雨飘零。在打开国门的洪流冲刷下,西学东渐带来的话语冲突第一次将黄公望及其传派推到了阻挡“ 历史洪流” 的保守一面,成为被扬弃与改造的对象。于是,在之后的岁月里,对于黄公望,文人画,乃至传统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改良与再造,草蛇灰线与推倒炉灶的轮回便不时上演,这还是在中国画辗转延续而来的脉络内部。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 再次启蒙” 的思潮兴起与西方现代主义之后的诸多影响的二次传入,中国画内部所萌发的自我现代化努力催生了“ 水墨画” 的概念,并在之后的时间里很快成为这一绘画领域面向当代语境时的“ 一体两面” 。而水墨艺术中的前卫实验者又与更激进的观念、行为艺术实验相结合,将水墨所继承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象征作为对象,以一种更具有“ 他者” 感的在场者身份参与到对话中来。于是,继承者、改良者、批判者、革新者、正视者、毁弃者、辗转于画中者、超脱于画外者,纷纷从各自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出发,以黄公望为一象征性的目标与大纛,通过一次次的“ 重写” 黄公望,做起自己针对中国画乃至中国文化的大文章。
在这里,之所以单举黄公望而不及其余,并不仅仅是因为本次展览的起始点为黄公望艺术,更因为在黄公望之后的语境中,他一直作为一种正统、温驯,有教养而可复制的典范存在,他的天才与修养是不可分离的,他的气质独特而温和,既不如倪瓒那般高不可攀,也不如王蒙那般灵气外显,这在技法上则表现为一种专业绘画的表现能力与文人推崇的笔墨趣味的微妙平衡。同时,如果参用方闻的理论,将元代绘画表述为一种从模拟性表现(mimetic representation) 到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的转化的话,那么,黄公望的“ 自我表现” 所体现的“ 人格迹化” 无疑是一种典正的文人气度及其“ 田园期待” 的体现。继而,从中国画的主体意识与客观特征两方面来看:无论是之后的明代中期文人群体壮大后的范式塑造,亦或是晚明变形主义趣味下的个性书写;无论是清初正统派的趣味继承与图式固化,亦或是野逸派的自我边缘与个性认同;无论是清末改革派由“ 四王” 上推黄公望的社会批判的图像递归,亦或是民国中期开始的追溯宋元的“ 复古革新” ;乃至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画在内部的自我现代化与外部的语境重塑中传统绘画题材的重新书写与观念化“ 再造” 中,黄公望都是一个典型的、重要的参照对象与话语起点。
黄公望以来的绘画传统,在当下的语境中,首先作为一种可以重新利用与再造的艺术资源而存在。这不仅包括从绘画内部自身沿革的角度出发,同时还可以从其他表现媒介与形式出发,将其作为一种语言重塑的对象,二次利用的媒材与激活传统的入口。这其中又可以从几个角度得到展现:其一,文人绘画的价值观念与当下语境的视觉经验的结合与再造,卢甫圣的山水艺术正是从中国山水的本体追求当代视觉样式的对位中找到了今天中国艺术的精神皈依与视觉逻辑;其二,中国绘画的主题趣味与西方绘画的形式构成之间的对接与对话,尚扬的《董其昌计划》系列正是建立在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方式上运用综合材料表达的代表性作品;其三,传统绘画的视觉再现与当代性的实验手法之间的嫁接与糅合,王天德在宣纸上运用烧烫燃灼的效果重新解剖传统山水图式来构成新一种艺术的空间维度;其四,“ 写山水法” 的艺术方法在不同艺术形式与观念语境中的重现与改造,徐冰的《背后的故事:富春山居图》、《芥子园山水卷》、《汉字的性格》等装置作品正是从观念视角进入传统语境并进行视觉方式再造的典型思维,从山水到文字,以激活传统来提炼当代的中国艺术智慧;其五,山水图式或者说观看方法向中国式的造景方法与空间体验的演绎与延伸,新媒体艺术作为当下离开传统山水绘画创作方式最远的艺术门类,却以一批艺术家对于山水乃至水墨资源的回归为新的起点,金江波的《诗意书写在自然》等一系列水墨互动影像艺术集中表现了中国传统观看方式与表现方式在与公众参与互动中形成的当代体验、再生与转换。这五种角度仅仅作为当下艺术生态的多元化思考的线索,他们共同的特征都是对传统经验的当下方法的重新开启。
另一个重要现象,黄公望以来的绘画传统,还作为一种艺术家实现自我文化认同的参照对象而存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史,是一部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对话对象不断变迁,但是主体关系一直稳定的艺术到政治的关系史。考察二十世纪艺术形态与趣味的发展规律,其变化与选择的内在逻辑,并不仅仅是艺术本体发展的结果,相反的,往往是一种当时的社会情境下一个艺术群体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反映。
二十世纪前期,在中西比较与对照的大语境中形成、发展起来的“ 中国画” 领域里,对待黄公望以降的绘画传统有着一个从批判到继承再造的过程。或者具体来说,“ 中国画” 概念的形成,首先脱胎于从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的世纪变革中,由文化性格批判投射到艺术形态上的文人画趣味的背离,从而完成艺术创作者身份与传统文人的洗脱。继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系列“ 国学” 建立的过程中,作为曾经的艺术典范的文人画图式与笔墨,开始与当时逐步更新的唐宋绘画资源与视觉经验,西方绘画理念与色彩经验,乃至一定程度上的时事化的题材相结合,形成了一种通过面向传统的视觉改造来获得更“ 自新” 乃至“ 革命” 的自我认同的“ 新中国画” 。这种徘徊于传统与革新之间的自我审查与投名状方式充斥在整个二十世纪并延续至今。岭南派的绘画作为与传统图式距离最远的一边,以民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奠定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政治视野中,融合派绘画趣味的“ 意识形态正统地位” ,这种趣味在1929年、1936年与1943年三届民国时期的“ 全国美展” 的国画展品与文本中表现的尤为充分。而建国后十七年间中国画的社会地位变化,则是从文化上的“ 正统代言” 到意识形态上的“ 政治改造” 的结果。艺术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化认同与意识形态立场做了背书。
盛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墨艺术,本质上也是中国画领域内部“ 自我现代化” 努力的结果,用水墨取代“ 中国画” ,是依靠材料语言来延续一种艺术种类内在的发展逻辑,从而可以顺利地抛弃由历史中层层叠加的视觉文化积累带来的传统负担,进而兼容不同程度的“ 离经叛道者” 。这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权宜之计。然而,当这种权宜之计成为新的客观存在的话语背景时,后来者就不得不接受这种将艺术材料与形式语言的结合作为自我认同的意义载体的设定,于是,从“ 画” 到“ 中国画” 再到“ 水墨画” 乃至“ 水墨艺术” ,这一艺术门类的视觉符号的底线也就从“ 士夫气” 、“ 笔墨” 、“ 纸笔” 、“ 水墨材料” 一路退守到“ 水墨观念” ,当水墨开始成为观念操弄的对象而不是实现的手段以后,它便开始走到了以材料语言视作识别标志的起点的反面。在当代语境中,继我们利用材料解脱形式、利用观念超越材料之后,如果“ 水墨” 不再用水和墨来创作,其边界究竟在哪里·
于是,在水墨艺术而不仅仅是水墨画的领域里,基于观念命题上的重写再一次追溯了传统与当代的两难选择,这便使得前述的问题进入了另一种“ 身份递归” 的解答之中,那就是:当下水墨艺术的定义,在于当下水墨艺术家做出的多样化实践。而对于水墨艺术家的界定何来,自我认同,艺术道路亦或是话语塑造?那么一个上述意义上的水墨艺术家,在其从水墨出发的艺术道路上,生长出一个超越既有的“ 水墨” 形式,是否就是当下水墨的观念前沿?一种艺术语言的延续生长与一种艺术视域的重归,何者才是当下的文化认同的底线逻辑?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的水墨热,除了原动力上的艺术市场因素外,从水墨艺术诞生的背景考察,是否还有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代性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下的焦虑,转向当下不断高涨的文化主体意识的结果?
从二十世纪以来的时间维度考察,黄公望背后的观念指向,从文人绘画的趣味传统转化为更广泛的文化传统;从传统绘画的图式符号资源到中国文化的艺术方法资源,从文化身份象征到文化问题。不变的是,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每一次对传统的继承都是重新书写,每一次重新书写都是再次创造,而每一次的再次创造又是在时代语境中确认自我的过程。在离开黄公望的日子里,我们一次次通过与前人的对话回到自己,同时也把他们带回我们身边。
由此,关于黄公望,关于黄公望以来的跌宕起伏的中国艺术史,关于今天对于曾经的创造的再一次审视与阐述,都将是不再道别的重写。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黄公望,一位成就了中国文人山水画成熟样式的代表艺术家,一位以艺术修养实现其作品“ 技进乎道” 的典型人物,一位被尊为“ 元四家” 之首,尤其被董其昌等后世推崇为“ 南宗” 的大师。于是,黄公望艺术便成为了中国文人绘画的代名词,又经历了几百年的摹学与演绎而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趣味。
值此,离开黄公望已660周年,今天我们再一次仰望大师,或许无有那种离开般的诗意和伤感,却是一种因为追忆形成的反思,一种对黄公望引发的半个多千年的艺术史演变过程的重读、重游与重写。
黄公望对后世的山水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从明代中期到清一代造就了主流的审美取向和历史文化语境。在其后层层累积的中国艺术史上,他作为一位具有开拓意义的里程碑人物,身后追随者的脚步不绝如缕。直至二十世纪初叶,伴随着国运日窘,中国绘画的历史境遇也随着时运流转而变得风雨飘零。在打开国门的洪流冲刷下,西学东渐带来的话语冲突第一次将黄公望及其传派推到了阻挡“ 历史洪流” 的保守一面,成为被扬弃与改造的对象。于是,在之后的岁月里,对于黄公望,文人画,乃至传统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改良与再造,草蛇灰线与推倒炉灶的轮回便不时上演,这还是在中国画辗转延续而来的脉络内部。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 再次启蒙” 的思潮兴起与西方现代主义之后的诸多影响的二次传入,中国画内部所萌发的自我现代化努力催生了“ 水墨画” 的概念,并在之后的时间里很快成为这一绘画领域面向当代语境时的“ 一体两面” 。而水墨艺术中的前卫实验者又与更激进的观念、行为艺术实验相结合,将水墨所继承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象征作为对象,以一种更具有“ 他者” 感的在场者身份参与到对话中来。于是,继承者、改良者、批判者、革新者、正视者、毁弃者、辗转于画中者、超脱于画外者,纷纷从各自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出发,以黄公望为一象征性的目标与大纛,通过一次次的“ 重写” 黄公望,做起自己针对中国画乃至中国文化的大文章。
在这里,之所以单举黄公望而不及其余,并不仅仅是因为本次展览的起始点为黄公望艺术,更因为在黄公望之后的语境中,他一直作为一种正统、温驯,有教养而可复制的典范存在,他的天才与修养是不可分离的,他的气质独特而温和,既不如倪瓒那般高不可攀,也不如王蒙那般灵气外显,这在技法上则表现为一种专业绘画的表现能力与文人推崇的笔墨趣味的微妙平衡。同时,如果参用方闻的理论,将元代绘画表述为一种从模拟性表现(mimetic representation) 到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的转化的话,那么,黄公望的“ 自我表现” 所体现的“ 人格迹化” 无疑是一种典正的文人气度及其“ 田园期待” 的体现。继而,从中国画的主体意识与客观特征两方面来看:无论是之后的明代中期文人群体壮大后的范式塑造,亦或是晚明变形主义趣味下的个性书写;无论是清初正统派的趣味继承与图式固化,亦或是野逸派的自我边缘与个性认同;无论是清末改革派由“ 四王” 上推黄公望的社会批判的图像递归,亦或是民国中期开始的追溯宋元的“ 复古革新” ;乃至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画在内部的自我现代化与外部的语境重塑中传统绘画题材的重新书写与观念化“ 再造” 中,黄公望都是一个典型的、重要的参照对象与话语起点。
黄公望以来的绘画传统,在当下的语境中,首先作为一种可以重新利用与再造的艺术资源而存在。这不仅包括从绘画内部自身沿革的角度出发,同时还可以从其他表现媒介与形式出发,将其作为一种语言重塑的对象,二次利用的媒材与激活传统的入口。这其中又可以从几个角度得到展现:其一,文人绘画的价值观念与当下语境的视觉经验的结合与再造,卢甫圣的山水艺术正是从中国山水的本体追求当代视觉样式的对位中找到了今天中国艺术的精神皈依与视觉逻辑;其二,中国绘画的主题趣味与西方绘画的形式构成之间的对接与对话,尚扬的《董其昌计划》系列正是建立在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方式上运用综合材料表达的代表性作品;其三,传统绘画的视觉再现与当代性的实验手法之间的嫁接与糅合,王天德在宣纸上运用烧烫燃灼的效果重新解剖传统山水图式来构成新一种艺术的空间维度;其四,“ 写山水法” 的艺术方法在不同艺术形式与观念语境中的重现与改造,徐冰的《背后的故事:富春山居图》、《芥子园山水卷》、《汉字的性格》等装置作品正是从观念视角进入传统语境并进行视觉方式再造的典型思维,从山水到文字,以激活传统来提炼当代的中国艺术智慧;其五,山水图式或者说观看方法向中国式的造景方法与空间体验的演绎与延伸,新媒体艺术作为当下离开传统山水绘画创作方式最远的艺术门类,却以一批艺术家对于山水乃至水墨资源的回归为新的起点,金江波的《诗意书写在自然》等一系列水墨互动影像艺术集中表现了中国传统观看方式与表现方式在与公众参与互动中形成的当代体验、再生与转换。这五种角度仅仅作为当下艺术生态的多元化思考的线索,他们共同的特征都是对传统经验的当下方法的重新开启。
另一个重要现象,黄公望以来的绘画传统,还作为一种艺术家实现自我文化认同的参照对象而存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史,是一部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对话对象不断变迁,但是主体关系一直稳定的艺术到政治的关系史。考察二十世纪艺术形态与趣味的发展规律,其变化与选择的内在逻辑,并不仅仅是艺术本体发展的结果,相反的,往往是一种当时的社会情境下一个艺术群体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反映。
二十世纪前期,在中西比较与对照的大语境中形成、发展起来的“ 中国画” 领域里,对待黄公望以降的绘画传统有着一个从批判到继承再造的过程。或者具体来说,“ 中国画” 概念的形成,首先脱胎于从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的世纪变革中,由文化性格批判投射到艺术形态上的文人画趣味的背离,从而完成艺术创作者身份与传统文人的洗脱。继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系列“ 国学” 建立的过程中,作为曾经的艺术典范的文人画图式与笔墨,开始与当时逐步更新的唐宋绘画资源与视觉经验,西方绘画理念与色彩经验,乃至一定程度上的时事化的题材相结合,形成了一种通过面向传统的视觉改造来获得更“ 自新” 乃至“ 革命” 的自我认同的“ 新中国画” 。这种徘徊于传统与革新之间的自我审查与投名状方式充斥在整个二十世纪并延续至今。岭南派的绘画作为与传统图式距离最远的一边,以民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奠定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政治视野中,融合派绘画趣味的“ 意识形态正统地位” ,这种趣味在1929年、1936年与1943年三届民国时期的“ 全国美展” 的国画展品与文本中表现的尤为充分。而建国后十七年间中国画的社会地位变化,则是从文化上的“ 正统代言” 到意识形态上的“ 政治改造” 的结果。艺术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化认同与意识形态立场做了背书。
盛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墨艺术,本质上也是中国画领域内部“ 自我现代化” 努力的结果,用水墨取代“ 中国画” ,是依靠材料语言来延续一种艺术种类内在的发展逻辑,从而可以顺利地抛弃由历史中层层叠加的视觉文化积累带来的传统负担,进而兼容不同程度的“ 离经叛道者” 。这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权宜之计。然而,当这种权宜之计成为新的客观存在的话语背景时,后来者就不得不接受这种将艺术材料与形式语言的结合作为自我认同的意义载体的设定,于是,从“ 画” 到“ 中国画” 再到“ 水墨画” 乃至“ 水墨艺术” ,这一艺术门类的视觉符号的底线也就从“ 士夫气” 、“ 笔墨” 、“ 纸笔” 、“ 水墨材料” 一路退守到“ 水墨观念” ,当水墨开始成为观念操弄的对象而不是实现的手段以后,它便开始走到了以材料语言视作识别标志的起点的反面。在当代语境中,继我们利用材料解脱形式、利用观念超越材料之后,如果“ 水墨” 不再用水和墨来创作,其边界究竟在哪里·
于是,在水墨艺术而不仅仅是水墨画的领域里,基于观念命题上的重写再一次追溯了传统与当代的两难选择,这便使得前述的问题进入了另一种“ 身份递归” 的解答之中,那就是:当下水墨艺术的定义,在于当下水墨艺术家做出的多样化实践。而对于水墨艺术家的界定何来,自我认同,艺术道路亦或是话语塑造?那么一个上述意义上的水墨艺术家,在其从水墨出发的艺术道路上,生长出一个超越既有的“ 水墨” 形式,是否就是当下水墨的观念前沿?一种艺术语言的延续生长与一种艺术视域的重归,何者才是当下的文化认同的底线逻辑?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的水墨热,除了原动力上的艺术市场因素外,从水墨艺术诞生的背景考察,是否还有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代性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下的焦虑,转向当下不断高涨的文化主体意识的结果?
从二十世纪以来的时间维度考察,黄公望背后的观念指向,从文人绘画的趣味传统转化为更广泛的文化传统;从传统绘画的图式符号资源到中国文化的艺术方法资源,从文化身份象征到文化问题。不变的是,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每一次对传统的继承都是重新书写,每一次重新书写都是再次创造,而每一次的再次创造又是在时代语境中确认自我的过程。在离开黄公望的日子里,我们一次次通过与前人的对话回到自己,同时也把他们带回我们身边。
由此,关于黄公望,关于黄公望以来的跌宕起伏的中国艺术史,关于今天对于曾经的创造的再一次审视与阐述,都将是不再道别的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