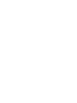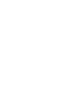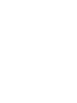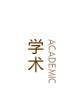漫道寻真——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关山月20世纪30、40年代西南、西北写生及其创作
2013-10-30 01:23:00来源:庞薰琹美术馆点击:5921
作 者:吴洪亮(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
出 版 社:湖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一
在苏立文先生所著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中文版序言的开篇部分,他这样写道:“ 1959年,当我出版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研究此课题的专著时,西方同行们批评我为一个不值得严肃对待的课题浪费时间。” [1]其实,何止是西方人,在中国美术通史的不少书籍中,文至清代也就结束了。20世纪被刻意地“ 似乎无意地” 回避,或许因为太近无法看清,或许因为存留了太多事与人的纷扰,或许因为我们自己缺少一套清晰的研究方法与评价体系,以至于对这样一个美术史课题长期失语了。而拿西方的一套评判标准来衡量20世纪的中国艺术时,又会陷入苏立文提到的两种现象的判定— — “ 没有新东西” 与“ 模仿西方” — — 之中。伴随着中国经济三十年的跳跃式发展,美术界的日趋自信,近十年来开始直面20世纪艺术的诸多问题,再加之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在商业上屡创天价,其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但研究与历史的发展一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今对20世纪中国艺术的研究恐怕还处于资料整理与举证的阶段,而无须急于进行全方位的价值判断。因此,许多机构开始了以个案为基础的研究工作。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日本的京都博物馆,还有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画院美术馆等相继推出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展览,其中关山月美术馆、庞薰琹美术馆则分别对关山月与庞薰琹进行了分专题的长期的资料搜集、整理、研究与展览,此次即将推出的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关山月20世纪30、40年代的写生及其创作的展览,则是对四位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专题性、断代式的比较,应该说是一次对具体艺术家个案进行交叉、比较与延伸的研究性展览项目。这一展览以选样或者说是切片的方式对中国艺术家在抗战的背景下所掀起的第一次到西部边疆地区写生、创作的浪潮,进行客观、对照式梳理,从而在对20世纪中国艺术这一创作的新方式与新题材研究的基础上,延展到对20世纪中国艺术的特殊性与价值的思考。这是对单纯个案考察后关联式的探求,所用的方法是从个案到个案与个案之间的比较研究,再到对时代特点的总结。笔者将这种方法称作“ 以个案勾勒整体” ,用一个更为形象的中国词语来形容则是“ 一叶知秋” 。
不仅如此,这样的研究展览还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对实在、可读、具有形象感的背景材料倍加重视;其次,对同一题材作品的图像对照更为视觉化,以便于理解;再次,让历史在同一空间与时间再次相遇,如同重新排演的一出戏剧,别有意趣。总之,以展览的形式呈现美术史的研究成果,是将美术史形象化的过程、活化的过程、传播的过程。
二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的中国,虽依旧处于动荡之中,但整体的社会发展是进入20世纪以来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甚至有把1927年到1937年称为“ 黃金十年” 的说法。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背景下,学术上的思考与争鸣也异常活跃。学者们的视野已不仅仅局限于书本与庙堂,而开始到那些所谓的“ 边远” 、“ 偏僻” 、“ 生疏” 地区进行研究考察,其理由是多方面的。比如在“ 西学东渐” 的背景下, 与“ 社会学” 、“ 人类学” 、“ 民族学” 、“ 博物学” 等相关学科引入中国有关。它们之间虽各有方向,但又存在交集,都涉及对人、社会、土地等方方面面的了解与认知,其中就包括对民间尤其是边疆民族的考察。192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说民族学》一文中指出:“ 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 他一直强调从艺术、交通、饮食、算术、币制、语言文字、音乐、宗教信仰八个方面研究各民族的发展脉络,强调“ 并非以新物全代旧物” 。这里触及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关系等问题。再有上世纪30年代以来,边疆频频发生变故,引起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关注,从政治方面以及经济、文化、教育方面,进行软性控制,甚至以宪法的方式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来作为民族政策的法理基础。
这些举措,也唤起了国内学界对边疆问题的全新思考。1934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徐益棠等学者特别关注对历史发展中的族群生态的研究,并尝试将其融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这种以所谓“ 科学” 为基础的了解国家各民族、各地区风土人情,吸收更广泛营养的方式,成为一时的风气。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诸多学者如周作人、顾颉刚、常惠、董作宾等都开始关注民间文艺学的研究。音乐方面则有赵元任对于民间音乐的开创性探索。梁思成所建构的“ 营造学社” 更以“ 田野考察” 的方式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实地研究。所以,这样的学术背景成为一大批学者、艺术家到西部地区进行考察的理论的支撑。
1939年,庞薰琹前往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就是因为当时中央博物院下达了考察任务,由此他开始了对西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艺术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的工作。在客观上,他从艺术的角度,凭借其艺术家的独特眼光收集了大量资料,并深入贵州少数民族的山寨,亲身体验婚礼、丧葬等活动且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与分析。以此为基础,庞薰琹创作出一批反映西南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构成了他由法国留学归来后创作的一个高峰。
孙宗慰的西北之行源于1925年张大千对敦煌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希望以一己之力前往敦煌考察、研究。1941年,孙宗慰在吕斯百的举荐下作为张大千的助手从重庆出发,踏上了西行之路。在敦煌孙宗慰帮助张大千进行了摹绘壁画、为洞窟编号等工作。在此行往返的路途中,孙宗慰对西北地区的民风地貌有了最为直观的了解与感悟。因此,这一临摹、考察活动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分水岭。
艺术家们在这一时期不约而同地进入西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大批高等院校的教师、众多学者汇聚到四川、云南等地,边远地区成为远离战争的治学之所。“ 在战争中逃亡滞留在内地的艺术家,他们在大西北、西南边陲和西藏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2]因此,事物的两面性充分地体现出来,学者、艺术家对于西部的研究与描绘成为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
三
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关山月这四位与西部结缘的艺术家应该说是20世纪中国艺坛在不同角度颇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庞薰琹涉猎广泛,包括绘画、广告、设计、装饰史研究等多个方面,更重要的,他是中国工艺美术及教育体系的奠基人。吴作人与孙宗慰同出自徐悲鸿门下,吴作人不仅在艺术上领一代风气,应该说更是徐悲鸿艺术体系最重要的继承者与推进者,孙宗慰则在绘画之外成为中国戏剧舞美基础教学体系的奠基人之一。关山月可谓是“ 岭南画派” 二高一陈之后的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到边疆写生与创作,不是偶然的孤例[3],而是一个时代内外因发酵的结果。这一行为是艺术家自发的、主动的与那片土地的一次更为纯真的接触。此次展览则是对这四位艺术家的断代研究,所以对他们之间的许多因缘关系,恐怕首先要梳理一下。
在这四人中最年长的是庞薰琹,1906年生于江苏常熟。1908年,吴作人生于江苏苏州。1912年7月,孙宗慰生于江苏常熟。1912年10月,关山月生于广东阳江。可见这四位中,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都是江苏人,庞薰琹与孙宗慰甚至是同乡,孙宗慰与关山月同是中华民国元年出生。庞薰琹与吴作人两位都留曾学欧洲,另两位则在本土完成了美术教育。40年代前后,他们先后到达西部,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位艺术家赴西南、西北的写生与创作成为他们艺术高峰期到来的起点。他们都去过敦煌,[4]对其艺术的临摹、研究与理解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节点。1949年之后,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同事。1957年之后,由于政治等原因,庞薰琹和孙宗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吴作人与关山月虽也历经磨难,但一直属于被光环所笼罩的艺术家。这样事实的产生,与历史有关,与他们个人有关,而产生的起点笔者以为源自他们选择的艺术道路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而西行则是产生这一结果的最早预兆。那么,我们就把目光汇集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他们的西部之行以及四位的交往与创作之中吧。
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关山月四位的边疆之缘,恐怕要感谢前文提到的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那一年,庞薰琹与齐白石、溥心畲、黄宾虹、王临乙、常书鸿等人同在国立北平艺专教书。由于战争形势紧迫,北平艺专南撤。1938年,与杭州艺专于湘西沅陵合并,改名为国立艺专。1939年秋,由梁思成、梁思永介绍,庞薰琹进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11月初,他开始在博物院从事西南少数民族艺术传统的研究。如前文所说,他承担了赴贵阳、花溪、龙里、贵定、安顺等八十多个苗族、仲家族村寨调查的任务 ,以收集当地的服饰、工艺、民谣民歌等民俗资料。这也激发了他在1941年创作了《黄果树瀑布》、《贵州山民图》20幅、《贵阳彝族洗衣图》、《苖人畅饮图》、《丧事》、《射牌》、《双人吹笙图》、《笙舞》等作品。1942年,创作了《橘红时节》、《盛装的苗族妇女》,成为他的代表性作品。庞薰琹的挚友苏立文曾描述他这一时期的作品:“ 表面上是民族学的记录,事实上远不止这些。因为这些作品将准确性与人情趣味、略带浪漫的格调,以及在巴黎所学得的对形式感的关注结合在一起。受毕加索的启发,他后来想到称此一时期的作品为他的‘灰色时期’。” [5]
吴作人于1935年回国,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那时孙宗慰是在校的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迁往重庆。1938年,吴作人组织“ 中央大学艺术系战地写生团” 开赴第五战区,在潢川、商丘等地画了大量速写,宣传抗战,孙宗慰是成员之一。1941年,如前文提到的,在吕斯百的推荐下,孙宗慰作为张大千的助手前往敦煌,对沿途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绘制了一大批该题材的作品。
同在1941年,关山月去四川嘉陵江、青城山、峨眉山写生,在贵阳、成都、重庆开“ 抗战画展” ,结识郭沫若、老舍、陶行知、黄君璧、刘开渠、赵望云、庞薰琹、侯宝璋、陈中凡、马鉴等。
1942年9月孙宗慰回到重庆,就职于中国美术学院。孙宗慰根据所见所闻及收集的资料完成的油画《蒙藏歌舞图》成为他一生中的重要作品。
1943年,吴作人到达成都。庞薰琹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我是1943年3月离开中央大学回到成都。生活更困难了。房租一涨再涨,只能把原来租的三间房中的最大一间退回给房东,后来吴作人来成都曾经租住过一个时期。” [6]此后,吴作人踏上了西北之行的征途,远赴兰州、西宁、敦煌写生、临摹壁画。几乎同期,关山月在重庆举办“ 西北风景写生画展” 后,偕妻子李秋璜和赵望云、张振铎同行,沿河西走廊奔赴敦煌。或许是由于机缘,吴作人与关山月在兰州相遇了,两人甚至骑在骆驼上互画了一张“ 小像” 。[7]关山月题“ 卅二年冬与作人兄骑明驼[8]互画留念时同客兰州 弟关山月” 。吴作人题“ 卅二年山月兄骑明驼互画留念 作人” 。可视为两位艺术家西行的逸闻趣事。关山月此行创作的《塞外驼铃》、《蒙民迁徙图》、《鞭马图》等同样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
1944年,吴作人回到成都与庞薰琹、刘开渠、雷圭元、丁聪、沈福文、秦威等组织“ 现代美术会” 。第一次展览会于华西大学学生俱乐部举行,当时展出了他的油画《祭青海》。
庞薰琹展出了《收割》、《跳花》、《小憩》、《赶集》等。这一年,孙宗慰则在重庆举办“ 西北写生画展” ,颇受好评。同一年,郭沫若为关山月《塞外驼铃》题诗六首,并对其作品题赞:“ 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喜见之。” 对写生作为创作的源泉的方法倍加肯定,期望尤甚。
1945年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年。3月,“ 现代美术会” 于四川美协展览馆举行第二次展览,共展出126件作品。关山月则将西南、西北写生画和部分敦煌临摹画于成都、重庆展出,并与赵望云、张振铎在重庆举办“ 西北写生画展” 。 吴作人在重庆举行“ 吴作人旅边画展” 。
1946年,吴作人在上海举行“ 吴作人边疆旅行画展” 之后,在徐悲鸿的召唤下同孙宗慰等人共赴北平,前往北平国立艺专任教。 徐悲鸿也同样聘请了庞薰琹,请他出任北平国立艺专图案系主任,庞未赴任,而是在次年前往广州,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广东省立艺专绘画系主任。1946年,关山月回广州任教于高剑父先生创办的南中画院。在广东文献馆举行“ 西南西北纪游画展” 。 而后去南洋写生半年,创作《椰林集市》、《印度姑娘》、《浴罢》等。1948年,关山月从南洋回广州,出版《西南、西北旅行纪游画选》及《南洋纪游画选》,庞薰琹为其作序。至此,本文对这四位艺术家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前后赴西南、西北写生、创作、展览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的情况大致做了叙述,从中提供的信息有几点值得注意:一、西部提供给他们新鲜的视野,激发了创作新面貌的形成;二、西部成为他们之间交往的重要纽带;三、这批作品成为其一生中的重要作品,随后的展览、出版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四
“ 写生” ,无论中西皆是个老话题,只是方式有些不同罢了。今天,我们提到的“ 写生” 总体的概念来自西方。西方的“ 写生” 是在现场完成的,最初仅是作为作品的图稿之用,在印象派之后现场、户外的写生则与作品紧密相连,甚至转化为作品本身了。这种方式,在20世纪初逐步进入中国的艺术教学体系,成为增进画艺的重要手段。20世纪的写生,是使被矫饰过的艺术重回真实的过程。这一行为与科学的实证因素有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先锋价值的。因为中国传统的艺术主流方式延续到四王,被康有为、徐悲鸿认为已经到了“ 死亡” 的时代,中国艺术的主观因素由于被过于强化,转而将一种自由变为了僵化,离自然所提供给我们的最直接、生动的信息太远了,艺术的活力没有了安身之地,所以写生是重拾面对真实世界的能力。
20世纪对于“ 写生” 这一方式无疑是幸运的,无论是社会的需求还是艺术生态的需求,都要求中国的艺术要从天回到地,开始重新关怀此时此刻的世界以及人本身。在西部,艺术家更可以自由地或不知不觉地试验着他们对不同学养、风格、刺激的融合。而这种松弛的表达使作品清新可读。当然,写生并非将客观的对象进行简单的位移,主观选择与过滤、个人手法、修养的渗入,也使写生及以写生为基础进行的创作体现出不同的风貌。尤其是这四位艺术家,他们在西部时期的写生与创作,虽然在对象上十分相似,但绘制的方法以及结果却是千差万别的。他们虽多有来往,但没有趋同的迹象,这应视为他们此时期创造的良性结果。
庞薰琹对服饰颇为客观的描绘与装饰化的呈现,孙宗慰对风俗情景化的表达以及主观的变形,吴作人将东、西艺术的不同方式自然地融入笔端,关山月因客体变换而变换的绘画手法,这一切都使写生变得丰富,以至于写生构成了一个可以被探讨的课题。除了形式,在创作理念上,这四位艺术家到西部所抱有的现实感召与理想诉求的结合,也使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朴素的具有个人风格的现实主义色彩,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追求又是一致的。
对于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关山月作品的具体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同与不同。
以关山月在四川、广西、贵阳、昆明等西南地区留下的第一批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作品为例,在这批写生作品中,有几个关键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对少数民族的形象与服饰图像的描绘,如《苗胞猎手》、《苗族少妇》等,其次是对他们典型的生活形态的刻画,如《负重》、《以作为息》、《织草履》、《农作去》、《归牧》等。在这些作品中,关山月的态度是灵活的,画法因需而变。如他对裙子的画法,就有勾线与没骨两种方式。在速写《待顾》以及创作《苗胞墟集图》中,裙子的形态使用细线勾勒然后着色的方式,呈现安然等待的状态。在《负重》中,他试图表现人行走的状态,即用没骨法,一笔下来既有裙子的形态,又呈现出人物的动势。当然,动与静是相对的,两种方式在关山月的作品中自由地出现,恐怕是他因时、因心境甚至因工具而变的。
同在贵州进行过创作的庞薰琹,其状态就与关山月大相径庭了。 庞薰琹“ 像绣花一般把许多花纹照原样地画上了画面” 。他自认为有些“ 苦闷而又低能” 。但他愿意 “ 尽量保存它原来面目” 。此时,庞薰琹更似一位学者,而关山月更像一位心态放松的艺术家,这恐怕和他们西行的出发点的差异有关,一个是进行田野式的考察,一个是进行自由的创作。在存世的关山月与庞薰琹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作品中有不少相同的题材,此处不妨对比一下。如同为描绘妇女的形象,虽一个为速写,一个为整理过的白描,姿态非常相似,画的方式却大不同。明显地关山月更注重对象的动态,用笔爽利,表明结构,虚实相间,重在说明问题。如人物右手在前,则以实线突显之,左手在后,则以细线勾勒,至下方几乎消失,意到即可。庞薰琹的人物白描在对衣纹装饰的准确描绘之外,更强调了人物姿态的美感、抒情性和装饰性。他笔笔到位,注重线条本身的韵律,尤其是帽子轮廓的线条以及腰带的线条,明显呈现出近处的部分粗重,远处的渐细的效果。不仅如此,庞薰琹在日后的教学中还强调,“ 线描不仅是物体轮廓的表现,线描本身还具有它自己的韵律,包括了形与意、虚与实、静与动、柔与刚种种变化。它一方面随着物质的“ 质” 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它又随着精神的“ 神” 的变化而变化。庞薰琹的理性与关山月的随机应变构成了不同的面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手中的毛笔都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呈现出中国笔墨韵味之外的西画透视的影子,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变革中的外化。
综上所述,庞薰琹作为中国的工艺美术大家,对装饰性更感兴趣,因此人物的形态、表情更为概括,也更为优美。关山月则注意抓住人物此时此刻的状态,将现实生活明明白白地留在画面之上。
孙宗慰遵从了徐悲鸿所说的“ 不但要走出画室面向自然对景写生,还要到生活中去” [9]。他的蒙藏生活的系列作品,不仅是对生活状态的记录,更从作品角度将民族的服饰之美彰显出来。这与庞薰琹对服饰的刻画不同,他更重视服饰对人物性格描绘的衬托作用,在其作品中甚至有一批专画背部形态的作品,每幅仅一人,背对画面,造型丰富、色彩艳丽的服饰使形体的变化更为风采绰约,由此引发观者更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摆脱了简单的对象描摹状态,而构成了写生基础上的创造。还有一组册页,他以平视安详的态度选取了当地人生活的不同侧面重新加以整理,将其情节化,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蒙藏风情图卷。这一系列作品,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是人物、动物造型的主观因素非常之多,甚至在进行有克制的变形。远山的处理不同于中国画山水的皴擦,更似西画,近景的人物则重线条之美,透视关系、骨骼关系被弱化了。尤其是人体转折处的线条,注重体现衣物的厚重感,而放弃了些许解剖的造型准确度。孙宗慰与吴作人、董希文西部写生最大的区别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变形,而这种变形又不同于后期印象派或野兽派的变形,它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其二是作品的色彩。或许是当地灿烂的阳光给了他不同的感受,孙宗慰一改早期作品的沉稳甚至有几分暗淡的色彩,转而运用明丽、清新的颜色,而且他甚至将色彩的淡雅与艳丽共融在一幅作品中。尤其是国画作品中的红色,今天看上去仿佛还在熠熠闪光。
说到造型和色彩,西北之行也给吴作人先生带来了明显的改变。在西北写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那里的阳光与景物的色彩进入了吴作人的画面,这不仅是色彩更为鲜亮的问题,而是有一股清新之风扫去了欧洲的雾霭,将作品的透明度提升了。那种松弛与单纯是西部留给作品最为清晰的印迹。再有就是吴作人绘制的没骨水墨人物与动物,一笔之下,造型、色彩与笔墨的语言尽现,这种手法在其后来的作品中很少见到了。
在西部提供给艺术家的多种素材中,不仅有风景、人物,还包括西北的动物:骆驼 、马、驴、狗、鹰等。而骆驼是生活在北方沙漠戈壁的一种最能吃苦耐劳的动物,也成为西北写生不可回避的对象。面对同一对象,几位艺术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在孙宗慰的作品中,他将骆驼进行了直接的拟人化的变形处理。他笔下的骆驼,大大的眼睛含情脉脉地看着你,恰似美女的妩媚,比旁边的人物都更加“ 抢镜” ,可见他对骆驼的情感与创作上的大胆。关山月恐怕就“ 客观” 得多。在《驼队之一》、《驼队之二》中,人物的形态与骆驼的姿态并重,画面流畅率真,笔墨因结构而生,可见此时他的造型能力已经非常娴熟,用笔爽利,也颇具信心。在此后的创作中,骆驼的形象也常常被运用,甚至成为主角。1943年的作品《塞外驼铃》与《驼运晚憩》中,则是将骆驼队行进与休憩的状态融入了画面的景致之中。 对于骆驼这一题材的运用,吴作人则走得更远。他在后来的创作中将其形象抽离,使描绘的笔墨程式化,如同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一样,他将骆驼演化为笔下的熟物,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化的载体。学者朱青生对此甚至进行了更为深入、精微的解读:“ 一个骆驼形象,到底是充分表现画者的意味,还是对象的精神?孰前孰后的问题,实际上是两条艺术道路的问题,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审美传统。在韩幹的马中,马不是马,而是雍容华贵;在吴作人的骆驼身上,骆驼就是骆驼,但却饱含着和人一样的理解和沉思。” [10]一番话将吴作人笔下的骆驼和古人所画的骆驼从概念上拉开了距离。
还有一点不容忽略,那个时期孙宗慰、吴作人、关山月先后前往敦煌,留下了不同的成果。孙宗慰在敦煌除了对千佛洞等景致写生之外,更多的是临摹,从他留下的多幅敦煌壁画的临摹作品来看,他不是刻板地重复,应该说他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体会与学养,不仅强化了线条之美,甚至有某种受过西画教育的体积、明暗之美。在其之后的佛教题材作品中更发展出不少个人的风格。吴作人先生不仅对敦煌壁画中的精彩片段进行了临习,更从中总结出了“ 概括” 二字的重要性,成为其日后颇具中国风范的油画创作以及中国画创作的基础。面对敦煌壁画,关山月秉承了他反复提到的创作方法:“ 我到西北写生,我采取的是在现场画简括的速写,回来加工提炼的方法。” [11]因此,对于敦煌的学习关山月的态度与面对造化的方法是一样的。他没有陷入具体的临习之中,在用“ 我法” 接近古人的丰厚资源。
庞薰琹在《关山月南洋旅行写生选》的序言中提道:“ 关山月有着这种变的精神,能跳出传统的牢笼。” 他甚至不惜将关山月与毕加索的“ 变” 进行比较。这样的类比是否贴切尚且不论,但关山月在“ 动” 中而“ 变” 的确成为他的特点。何止关山月,每一位来到西部的艺术家都在发生变化,各自建构着自己的创作方法,从而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艺术探索之路。
五
20世纪中国艺术纷繁而纠结的面貌是基于什么而产生的?那些被潘公凯先生称作“ 自觉” 的动能与怎样的 “ 革新” 意识有关?在日本的侵略与我们的反抗成为长期的、日常的状态之后,艺术家们前往边疆考察与写生的行为是对民族、国家以及自我意识的求证吗?这样的求证,这样描绘的本体价值在美术史中会是什么位置?20世纪的中国艺术的确给我们留下了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并进行更为明确的判断。
诚然,20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变化是中国艺术原有独特性日渐模糊的过程,也是新的独特性逐步形成的过程。艺术家开始了不同于传统意识的创造,这对于国人和外国人都是不习惯的,甚至是陌生的。很长时间以来它如同青春期的孩子,长得有些纠结而缺少关爱。如今,由于大环境的改变,时间与判定方法的变化,我们是否可以平静地面对了?而且对“ 坚守” 与“ 融合” 这样的旧问题的反思,于今天依然具有意义。因为20世纪的中国艺术无可回避地已经成为传统的一个部分,对它的探求正是对当代艺术思想、创作方式的寻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30、40年代到西部的写生与创作是将单纯的形式主义追求与技法的诉求,拉回到与现实世界相关的艺术范畴中进行思考与表达的过程。因此,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庞薰琹找到了可供表达、转换乃至设计的源泉;吴作人找到了清亮的光、色与升华的可能;孙宗慰找到了使形象自然变形的途径以及固有色彩的魅力;关山月则在“ 动” 与“ 画” 之间,寻觅到了创作的动能与社会交流的方法。所以西部的写生与创作,借由户外富氧的环境与对艺术的思考、实践、凝聚、溶解、升华的过程,由个人化的举动到小群体化的共识,再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被设定为可进入历史思考的现象。此结果是以这批艺术家的责任与理想为动因,以青春与真诚所建构的,从而使这段历史充满了活力。
回望20世纪30、40年代的西部写生及其创作,我们也不得不与1949年之后,50至60年代的写生相对应来思考。这一时期的写生在1942年延安座谈会讲话的同期,其行为还停留在研究、探索的学术层面,功利地,让艺术成为改造世界的工具以及服务的功能尚在清晰与不清晰间游走,作品相对是平和的,没有被僵化的现实主义所干扰。这种还未背负着某种既定主义和先验观点去观察世界的行为,是对何为“ 真” 的朴素的、原发的追问。
今天对这一过往现象的探究与通过展览的形式进行再现,如慢饮一杯柠檬水,使我们掺杂了过多历史油腻的身心清爽了许多;更似细品一杯午后的红茶,让时光的味道愈加醇厚,杳然入心。
(注:本文部分内容引自笔者在做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关山月四位艺术家个案研究或展览时所写的相关文章。)
注释:
1.〔英〕迈克尔•苏立文著,陈卫和、钱岗南译 《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上),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1页。
2.〔英〕M.苏立文著、陈瑞林译《东西方美术的交流》,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8年,第 216页。
3. 1934年开始,赵望云由唐山经八达岭、张家口、大同至内蒙古草原,开西北写生之先河。1943年7月至1945年冬,董希文沿重庆-敦煌-南疆公路(同常书鸿)-敦煌-兰州一路写生。1943年,司徒乔到新疆等西北地区写生。1945和1948年,黄胄跟随其师赵望云到西北写生。还有韩乐然等的西北写生,叶浅予等的西南写生,构成了一个时期的艺术景观。
4.庞薰琹一直在对敦煌进行研究。1978年,在《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即将出版时,他将出版计划延迟一年,前往敦煌考察,圆了自己的“ 敦煌梦” ,也因为这次敦煌之行,对该书进行了最后的修订。
5.〔英〕迈克尔•苏立文著,陈卫和、钱岗南译《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上),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5页。
6.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2页。
7.吴作人百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吴作人年谱 (待定本)》。
8.指善走的骆驼。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毛篇》:“ 驼,性羞。《木兰》篇‘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
9. 1983年“ 孙宗慰遗作展” 研讨会冯法祀发言。
10.朱青生、吴宁主编《当代书画家第一辑吴作人素描基础:新中国画的革命?》, 中国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 58页。
11.《我所走过的艺术道路— — 在一个座谈会上的谈话》,摘自《乡心无限》,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出 版 社:湖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一
在苏立文先生所著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中文版序言的开篇部分,他这样写道:“ 1959年,当我出版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研究此课题的专著时,西方同行们批评我为一个不值得严肃对待的课题浪费时间。” [1]其实,何止是西方人,在中国美术通史的不少书籍中,文至清代也就结束了。20世纪被刻意地“ 似乎无意地” 回避,或许因为太近无法看清,或许因为存留了太多事与人的纷扰,或许因为我们自己缺少一套清晰的研究方法与评价体系,以至于对这样一个美术史课题长期失语了。而拿西方的一套评判标准来衡量20世纪的中国艺术时,又会陷入苏立文提到的两种现象的判定— — “ 没有新东西” 与“ 模仿西方” — — 之中。伴随着中国经济三十年的跳跃式发展,美术界的日趋自信,近十年来开始直面20世纪艺术的诸多问题,再加之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在商业上屡创天价,其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但研究与历史的发展一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今对20世纪中国艺术的研究恐怕还处于资料整理与举证的阶段,而无须急于进行全方位的价值判断。因此,许多机构开始了以个案为基础的研究工作。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日本的京都博物馆,还有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画院美术馆等相继推出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展览,其中关山月美术馆、庞薰琹美术馆则分别对关山月与庞薰琹进行了分专题的长期的资料搜集、整理、研究与展览,此次即将推出的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关山月20世纪30、40年代的写生及其创作的展览,则是对四位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专题性、断代式的比较,应该说是一次对具体艺术家个案进行交叉、比较与延伸的研究性展览项目。这一展览以选样或者说是切片的方式对中国艺术家在抗战的背景下所掀起的第一次到西部边疆地区写生、创作的浪潮,进行客观、对照式梳理,从而在对20世纪中国艺术这一创作的新方式与新题材研究的基础上,延展到对20世纪中国艺术的特殊性与价值的思考。这是对单纯个案考察后关联式的探求,所用的方法是从个案到个案与个案之间的比较研究,再到对时代特点的总结。笔者将这种方法称作“ 以个案勾勒整体” ,用一个更为形象的中国词语来形容则是“ 一叶知秋” 。
不仅如此,这样的研究展览还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对实在、可读、具有形象感的背景材料倍加重视;其次,对同一题材作品的图像对照更为视觉化,以便于理解;再次,让历史在同一空间与时间再次相遇,如同重新排演的一出戏剧,别有意趣。总之,以展览的形式呈现美术史的研究成果,是将美术史形象化的过程、活化的过程、传播的过程。
二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的中国,虽依旧处于动荡之中,但整体的社会发展是进入20世纪以来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甚至有把1927年到1937年称为“ 黃金十年” 的说法。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背景下,学术上的思考与争鸣也异常活跃。学者们的视野已不仅仅局限于书本与庙堂,而开始到那些所谓的“ 边远” 、“ 偏僻” 、“ 生疏” 地区进行研究考察,其理由是多方面的。比如在“ 西学东渐” 的背景下, 与“ 社会学” 、“ 人类学” 、“ 民族学” 、“ 博物学” 等相关学科引入中国有关。它们之间虽各有方向,但又存在交集,都涉及对人、社会、土地等方方面面的了解与认知,其中就包括对民间尤其是边疆民族的考察。192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说民族学》一文中指出:“ 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 他一直强调从艺术、交通、饮食、算术、币制、语言文字、音乐、宗教信仰八个方面研究各民族的发展脉络,强调“ 并非以新物全代旧物” 。这里触及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关系等问题。再有上世纪30年代以来,边疆频频发生变故,引起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关注,从政治方面以及经济、文化、教育方面,进行软性控制,甚至以宪法的方式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来作为民族政策的法理基础。
这些举措,也唤起了国内学界对边疆问题的全新思考。1934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徐益棠等学者特别关注对历史发展中的族群生态的研究,并尝试将其融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这种以所谓“ 科学” 为基础的了解国家各民族、各地区风土人情,吸收更广泛营养的方式,成为一时的风气。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诸多学者如周作人、顾颉刚、常惠、董作宾等都开始关注民间文艺学的研究。音乐方面则有赵元任对于民间音乐的开创性探索。梁思成所建构的“ 营造学社” 更以“ 田野考察” 的方式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实地研究。所以,这样的学术背景成为一大批学者、艺术家到西部地区进行考察的理论的支撑。
1939年,庞薰琹前往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就是因为当时中央博物院下达了考察任务,由此他开始了对西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艺术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的工作。在客观上,他从艺术的角度,凭借其艺术家的独特眼光收集了大量资料,并深入贵州少数民族的山寨,亲身体验婚礼、丧葬等活动且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与分析。以此为基础,庞薰琹创作出一批反映西南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构成了他由法国留学归来后创作的一个高峰。
孙宗慰的西北之行源于1925年张大千对敦煌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希望以一己之力前往敦煌考察、研究。1941年,孙宗慰在吕斯百的举荐下作为张大千的助手从重庆出发,踏上了西行之路。在敦煌孙宗慰帮助张大千进行了摹绘壁画、为洞窟编号等工作。在此行往返的路途中,孙宗慰对西北地区的民风地貌有了最为直观的了解与感悟。因此,这一临摹、考察活动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分水岭。
艺术家们在这一时期不约而同地进入西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大批高等院校的教师、众多学者汇聚到四川、云南等地,边远地区成为远离战争的治学之所。“ 在战争中逃亡滞留在内地的艺术家,他们在大西北、西南边陲和西藏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2]因此,事物的两面性充分地体现出来,学者、艺术家对于西部的研究与描绘成为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
三
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关山月这四位与西部结缘的艺术家应该说是20世纪中国艺坛在不同角度颇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庞薰琹涉猎广泛,包括绘画、广告、设计、装饰史研究等多个方面,更重要的,他是中国工艺美术及教育体系的奠基人。吴作人与孙宗慰同出自徐悲鸿门下,吴作人不仅在艺术上领一代风气,应该说更是徐悲鸿艺术体系最重要的继承者与推进者,孙宗慰则在绘画之外成为中国戏剧舞美基础教学体系的奠基人之一。关山月可谓是“ 岭南画派” 二高一陈之后的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到边疆写生与创作,不是偶然的孤例[3],而是一个时代内外因发酵的结果。这一行为是艺术家自发的、主动的与那片土地的一次更为纯真的接触。此次展览则是对这四位艺术家的断代研究,所以对他们之间的许多因缘关系,恐怕首先要梳理一下。
在这四人中最年长的是庞薰琹,1906年生于江苏常熟。1908年,吴作人生于江苏苏州。1912年7月,孙宗慰生于江苏常熟。1912年10月,关山月生于广东阳江。可见这四位中,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都是江苏人,庞薰琹与孙宗慰甚至是同乡,孙宗慰与关山月同是中华民国元年出生。庞薰琹与吴作人两位都留曾学欧洲,另两位则在本土完成了美术教育。40年代前后,他们先后到达西部,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位艺术家赴西南、西北的写生与创作成为他们艺术高峰期到来的起点。他们都去过敦煌,[4]对其艺术的临摹、研究与理解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节点。1949年之后,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同事。1957年之后,由于政治等原因,庞薰琹和孙宗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吴作人与关山月虽也历经磨难,但一直属于被光环所笼罩的艺术家。这样事实的产生,与历史有关,与他们个人有关,而产生的起点笔者以为源自他们选择的艺术道路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而西行则是产生这一结果的最早预兆。那么,我们就把目光汇集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他们的西部之行以及四位的交往与创作之中吧。
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关山月四位的边疆之缘,恐怕要感谢前文提到的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那一年,庞薰琹与齐白石、溥心畲、黄宾虹、王临乙、常书鸿等人同在国立北平艺专教书。由于战争形势紧迫,北平艺专南撤。1938年,与杭州艺专于湘西沅陵合并,改名为国立艺专。1939年秋,由梁思成、梁思永介绍,庞薰琹进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11月初,他开始在博物院从事西南少数民族艺术传统的研究。如前文所说,他承担了赴贵阳、花溪、龙里、贵定、安顺等八十多个苗族、仲家族村寨调查的任务 ,以收集当地的服饰、工艺、民谣民歌等民俗资料。这也激发了他在1941年创作了《黄果树瀑布》、《贵州山民图》20幅、《贵阳彝族洗衣图》、《苖人畅饮图》、《丧事》、《射牌》、《双人吹笙图》、《笙舞》等作品。1942年,创作了《橘红时节》、《盛装的苗族妇女》,成为他的代表性作品。庞薰琹的挚友苏立文曾描述他这一时期的作品:“ 表面上是民族学的记录,事实上远不止这些。因为这些作品将准确性与人情趣味、略带浪漫的格调,以及在巴黎所学得的对形式感的关注结合在一起。受毕加索的启发,他后来想到称此一时期的作品为他的‘灰色时期’。” [5]
吴作人于1935年回国,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那时孙宗慰是在校的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迁往重庆。1938年,吴作人组织“ 中央大学艺术系战地写生团” 开赴第五战区,在潢川、商丘等地画了大量速写,宣传抗战,孙宗慰是成员之一。1941年,如前文提到的,在吕斯百的推荐下,孙宗慰作为张大千的助手前往敦煌,对沿途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绘制了一大批该题材的作品。
同在1941年,关山月去四川嘉陵江、青城山、峨眉山写生,在贵阳、成都、重庆开“ 抗战画展” ,结识郭沫若、老舍、陶行知、黄君璧、刘开渠、赵望云、庞薰琹、侯宝璋、陈中凡、马鉴等。
1942年9月孙宗慰回到重庆,就职于中国美术学院。孙宗慰根据所见所闻及收集的资料完成的油画《蒙藏歌舞图》成为他一生中的重要作品。
1943年,吴作人到达成都。庞薰琹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我是1943年3月离开中央大学回到成都。生活更困难了。房租一涨再涨,只能把原来租的三间房中的最大一间退回给房东,后来吴作人来成都曾经租住过一个时期。” [6]此后,吴作人踏上了西北之行的征途,远赴兰州、西宁、敦煌写生、临摹壁画。几乎同期,关山月在重庆举办“ 西北风景写生画展” 后,偕妻子李秋璜和赵望云、张振铎同行,沿河西走廊奔赴敦煌。或许是由于机缘,吴作人与关山月在兰州相遇了,两人甚至骑在骆驼上互画了一张“ 小像” 。[7]关山月题“ 卅二年冬与作人兄骑明驼[8]互画留念时同客兰州 弟关山月” 。吴作人题“ 卅二年山月兄骑明驼互画留念 作人” 。可视为两位艺术家西行的逸闻趣事。关山月此行创作的《塞外驼铃》、《蒙民迁徙图》、《鞭马图》等同样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
1944年,吴作人回到成都与庞薰琹、刘开渠、雷圭元、丁聪、沈福文、秦威等组织“ 现代美术会” 。第一次展览会于华西大学学生俱乐部举行,当时展出了他的油画《祭青海》。
庞薰琹展出了《收割》、《跳花》、《小憩》、《赶集》等。这一年,孙宗慰则在重庆举办“ 西北写生画展” ,颇受好评。同一年,郭沫若为关山月《塞外驼铃》题诗六首,并对其作品题赞:“ 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喜见之。” 对写生作为创作的源泉的方法倍加肯定,期望尤甚。
1945年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年。3月,“ 现代美术会” 于四川美协展览馆举行第二次展览,共展出126件作品。关山月则将西南、西北写生画和部分敦煌临摹画于成都、重庆展出,并与赵望云、张振铎在重庆举办“ 西北写生画展” 。 吴作人在重庆举行“ 吴作人旅边画展” 。
1946年,吴作人在上海举行“ 吴作人边疆旅行画展” 之后,在徐悲鸿的召唤下同孙宗慰等人共赴北平,前往北平国立艺专任教。 徐悲鸿也同样聘请了庞薰琹,请他出任北平国立艺专图案系主任,庞未赴任,而是在次年前往广州,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广东省立艺专绘画系主任。1946年,关山月回广州任教于高剑父先生创办的南中画院。在广东文献馆举行“ 西南西北纪游画展” 。 而后去南洋写生半年,创作《椰林集市》、《印度姑娘》、《浴罢》等。1948年,关山月从南洋回广州,出版《西南、西北旅行纪游画选》及《南洋纪游画选》,庞薰琹为其作序。至此,本文对这四位艺术家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前后赴西南、西北写生、创作、展览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的情况大致做了叙述,从中提供的信息有几点值得注意:一、西部提供给他们新鲜的视野,激发了创作新面貌的形成;二、西部成为他们之间交往的重要纽带;三、这批作品成为其一生中的重要作品,随后的展览、出版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四
“ 写生” ,无论中西皆是个老话题,只是方式有些不同罢了。今天,我们提到的“ 写生” 总体的概念来自西方。西方的“ 写生” 是在现场完成的,最初仅是作为作品的图稿之用,在印象派之后现场、户外的写生则与作品紧密相连,甚至转化为作品本身了。这种方式,在20世纪初逐步进入中国的艺术教学体系,成为增进画艺的重要手段。20世纪的写生,是使被矫饰过的艺术重回真实的过程。这一行为与科学的实证因素有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先锋价值的。因为中国传统的艺术主流方式延续到四王,被康有为、徐悲鸿认为已经到了“ 死亡” 的时代,中国艺术的主观因素由于被过于强化,转而将一种自由变为了僵化,离自然所提供给我们的最直接、生动的信息太远了,艺术的活力没有了安身之地,所以写生是重拾面对真实世界的能力。
20世纪对于“ 写生” 这一方式无疑是幸运的,无论是社会的需求还是艺术生态的需求,都要求中国的艺术要从天回到地,开始重新关怀此时此刻的世界以及人本身。在西部,艺术家更可以自由地或不知不觉地试验着他们对不同学养、风格、刺激的融合。而这种松弛的表达使作品清新可读。当然,写生并非将客观的对象进行简单的位移,主观选择与过滤、个人手法、修养的渗入,也使写生及以写生为基础进行的创作体现出不同的风貌。尤其是这四位艺术家,他们在西部时期的写生与创作,虽然在对象上十分相似,但绘制的方法以及结果却是千差万别的。他们虽多有来往,但没有趋同的迹象,这应视为他们此时期创造的良性结果。
庞薰琹对服饰颇为客观的描绘与装饰化的呈现,孙宗慰对风俗情景化的表达以及主观的变形,吴作人将东、西艺术的不同方式自然地融入笔端,关山月因客体变换而变换的绘画手法,这一切都使写生变得丰富,以至于写生构成了一个可以被探讨的课题。除了形式,在创作理念上,这四位艺术家到西部所抱有的现实感召与理想诉求的结合,也使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朴素的具有个人风格的现实主义色彩,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追求又是一致的。
对于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关山月作品的具体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同与不同。
以关山月在四川、广西、贵阳、昆明等西南地区留下的第一批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作品为例,在这批写生作品中,有几个关键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对少数民族的形象与服饰图像的描绘,如《苗胞猎手》、《苗族少妇》等,其次是对他们典型的生活形态的刻画,如《负重》、《以作为息》、《织草履》、《农作去》、《归牧》等。在这些作品中,关山月的态度是灵活的,画法因需而变。如他对裙子的画法,就有勾线与没骨两种方式。在速写《待顾》以及创作《苗胞墟集图》中,裙子的形态使用细线勾勒然后着色的方式,呈现安然等待的状态。在《负重》中,他试图表现人行走的状态,即用没骨法,一笔下来既有裙子的形态,又呈现出人物的动势。当然,动与静是相对的,两种方式在关山月的作品中自由地出现,恐怕是他因时、因心境甚至因工具而变的。
同在贵州进行过创作的庞薰琹,其状态就与关山月大相径庭了。 庞薰琹“ 像绣花一般把许多花纹照原样地画上了画面” 。他自认为有些“ 苦闷而又低能” 。但他愿意 “ 尽量保存它原来面目” 。此时,庞薰琹更似一位学者,而关山月更像一位心态放松的艺术家,这恐怕和他们西行的出发点的差异有关,一个是进行田野式的考察,一个是进行自由的创作。在存世的关山月与庞薰琹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作品中有不少相同的题材,此处不妨对比一下。如同为描绘妇女的形象,虽一个为速写,一个为整理过的白描,姿态非常相似,画的方式却大不同。明显地关山月更注重对象的动态,用笔爽利,表明结构,虚实相间,重在说明问题。如人物右手在前,则以实线突显之,左手在后,则以细线勾勒,至下方几乎消失,意到即可。庞薰琹的人物白描在对衣纹装饰的准确描绘之外,更强调了人物姿态的美感、抒情性和装饰性。他笔笔到位,注重线条本身的韵律,尤其是帽子轮廓的线条以及腰带的线条,明显呈现出近处的部分粗重,远处的渐细的效果。不仅如此,庞薰琹在日后的教学中还强调,“ 线描不仅是物体轮廓的表现,线描本身还具有它自己的韵律,包括了形与意、虚与实、静与动、柔与刚种种变化。它一方面随着物质的“ 质” 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它又随着精神的“ 神” 的变化而变化。庞薰琹的理性与关山月的随机应变构成了不同的面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手中的毛笔都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呈现出中国笔墨韵味之外的西画透视的影子,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变革中的外化。
综上所述,庞薰琹作为中国的工艺美术大家,对装饰性更感兴趣,因此人物的形态、表情更为概括,也更为优美。关山月则注意抓住人物此时此刻的状态,将现实生活明明白白地留在画面之上。
孙宗慰遵从了徐悲鸿所说的“ 不但要走出画室面向自然对景写生,还要到生活中去” [9]。他的蒙藏生活的系列作品,不仅是对生活状态的记录,更从作品角度将民族的服饰之美彰显出来。这与庞薰琹对服饰的刻画不同,他更重视服饰对人物性格描绘的衬托作用,在其作品中甚至有一批专画背部形态的作品,每幅仅一人,背对画面,造型丰富、色彩艳丽的服饰使形体的变化更为风采绰约,由此引发观者更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摆脱了简单的对象描摹状态,而构成了写生基础上的创造。还有一组册页,他以平视安详的态度选取了当地人生活的不同侧面重新加以整理,将其情节化,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蒙藏风情图卷。这一系列作品,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是人物、动物造型的主观因素非常之多,甚至在进行有克制的变形。远山的处理不同于中国画山水的皴擦,更似西画,近景的人物则重线条之美,透视关系、骨骼关系被弱化了。尤其是人体转折处的线条,注重体现衣物的厚重感,而放弃了些许解剖的造型准确度。孙宗慰与吴作人、董希文西部写生最大的区别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变形,而这种变形又不同于后期印象派或野兽派的变形,它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其二是作品的色彩。或许是当地灿烂的阳光给了他不同的感受,孙宗慰一改早期作品的沉稳甚至有几分暗淡的色彩,转而运用明丽、清新的颜色,而且他甚至将色彩的淡雅与艳丽共融在一幅作品中。尤其是国画作品中的红色,今天看上去仿佛还在熠熠闪光。
说到造型和色彩,西北之行也给吴作人先生带来了明显的改变。在西北写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那里的阳光与景物的色彩进入了吴作人的画面,这不仅是色彩更为鲜亮的问题,而是有一股清新之风扫去了欧洲的雾霭,将作品的透明度提升了。那种松弛与单纯是西部留给作品最为清晰的印迹。再有就是吴作人绘制的没骨水墨人物与动物,一笔之下,造型、色彩与笔墨的语言尽现,这种手法在其后来的作品中很少见到了。
在西部提供给艺术家的多种素材中,不仅有风景、人物,还包括西北的动物:骆驼 、马、驴、狗、鹰等。而骆驼是生活在北方沙漠戈壁的一种最能吃苦耐劳的动物,也成为西北写生不可回避的对象。面对同一对象,几位艺术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在孙宗慰的作品中,他将骆驼进行了直接的拟人化的变形处理。他笔下的骆驼,大大的眼睛含情脉脉地看着你,恰似美女的妩媚,比旁边的人物都更加“ 抢镜” ,可见他对骆驼的情感与创作上的大胆。关山月恐怕就“ 客观” 得多。在《驼队之一》、《驼队之二》中,人物的形态与骆驼的姿态并重,画面流畅率真,笔墨因结构而生,可见此时他的造型能力已经非常娴熟,用笔爽利,也颇具信心。在此后的创作中,骆驼的形象也常常被运用,甚至成为主角。1943年的作品《塞外驼铃》与《驼运晚憩》中,则是将骆驼队行进与休憩的状态融入了画面的景致之中。 对于骆驼这一题材的运用,吴作人则走得更远。他在后来的创作中将其形象抽离,使描绘的笔墨程式化,如同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一样,他将骆驼演化为笔下的熟物,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化的载体。学者朱青生对此甚至进行了更为深入、精微的解读:“ 一个骆驼形象,到底是充分表现画者的意味,还是对象的精神?孰前孰后的问题,实际上是两条艺术道路的问题,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审美传统。在韩幹的马中,马不是马,而是雍容华贵;在吴作人的骆驼身上,骆驼就是骆驼,但却饱含着和人一样的理解和沉思。” [10]一番话将吴作人笔下的骆驼和古人所画的骆驼从概念上拉开了距离。
还有一点不容忽略,那个时期孙宗慰、吴作人、关山月先后前往敦煌,留下了不同的成果。孙宗慰在敦煌除了对千佛洞等景致写生之外,更多的是临摹,从他留下的多幅敦煌壁画的临摹作品来看,他不是刻板地重复,应该说他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体会与学养,不仅强化了线条之美,甚至有某种受过西画教育的体积、明暗之美。在其之后的佛教题材作品中更发展出不少个人的风格。吴作人先生不仅对敦煌壁画中的精彩片段进行了临习,更从中总结出了“ 概括” 二字的重要性,成为其日后颇具中国风范的油画创作以及中国画创作的基础。面对敦煌壁画,关山月秉承了他反复提到的创作方法:“ 我到西北写生,我采取的是在现场画简括的速写,回来加工提炼的方法。” [11]因此,对于敦煌的学习关山月的态度与面对造化的方法是一样的。他没有陷入具体的临习之中,在用“ 我法” 接近古人的丰厚资源。
庞薰琹在《关山月南洋旅行写生选》的序言中提道:“ 关山月有着这种变的精神,能跳出传统的牢笼。” 他甚至不惜将关山月与毕加索的“ 变” 进行比较。这样的类比是否贴切尚且不论,但关山月在“ 动” 中而“ 变” 的确成为他的特点。何止关山月,每一位来到西部的艺术家都在发生变化,各自建构着自己的创作方法,从而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艺术探索之路。
五
20世纪中国艺术纷繁而纠结的面貌是基于什么而产生的?那些被潘公凯先生称作“ 自觉” 的动能与怎样的 “ 革新” 意识有关?在日本的侵略与我们的反抗成为长期的、日常的状态之后,艺术家们前往边疆考察与写生的行为是对民族、国家以及自我意识的求证吗?这样的求证,这样描绘的本体价值在美术史中会是什么位置?20世纪的中国艺术的确给我们留下了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并进行更为明确的判断。
诚然,20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变化是中国艺术原有独特性日渐模糊的过程,也是新的独特性逐步形成的过程。艺术家开始了不同于传统意识的创造,这对于国人和外国人都是不习惯的,甚至是陌生的。很长时间以来它如同青春期的孩子,长得有些纠结而缺少关爱。如今,由于大环境的改变,时间与判定方法的变化,我们是否可以平静地面对了?而且对“ 坚守” 与“ 融合” 这样的旧问题的反思,于今天依然具有意义。因为20世纪的中国艺术无可回避地已经成为传统的一个部分,对它的探求正是对当代艺术思想、创作方式的寻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30、40年代到西部的写生与创作是将单纯的形式主义追求与技法的诉求,拉回到与现实世界相关的艺术范畴中进行思考与表达的过程。因此,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庞薰琹找到了可供表达、转换乃至设计的源泉;吴作人找到了清亮的光、色与升华的可能;孙宗慰找到了使形象自然变形的途径以及固有色彩的魅力;关山月则在“ 动” 与“ 画” 之间,寻觅到了创作的动能与社会交流的方法。所以西部的写生与创作,借由户外富氧的环境与对艺术的思考、实践、凝聚、溶解、升华的过程,由个人化的举动到小群体化的共识,再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被设定为可进入历史思考的现象。此结果是以这批艺术家的责任与理想为动因,以青春与真诚所建构的,从而使这段历史充满了活力。
回望20世纪30、40年代的西部写生及其创作,我们也不得不与1949年之后,50至60年代的写生相对应来思考。这一时期的写生在1942年延安座谈会讲话的同期,其行为还停留在研究、探索的学术层面,功利地,让艺术成为改造世界的工具以及服务的功能尚在清晰与不清晰间游走,作品相对是平和的,没有被僵化的现实主义所干扰。这种还未背负着某种既定主义和先验观点去观察世界的行为,是对何为“ 真” 的朴素的、原发的追问。
今天对这一过往现象的探究与通过展览的形式进行再现,如慢饮一杯柠檬水,使我们掺杂了过多历史油腻的身心清爽了许多;更似细品一杯午后的红茶,让时光的味道愈加醇厚,杳然入心。
(注:本文部分内容引自笔者在做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关山月四位艺术家个案研究或展览时所写的相关文章。)
注释:
1.〔英〕迈克尔•苏立文著,陈卫和、钱岗南译 《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上),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1页。
2.〔英〕M.苏立文著、陈瑞林译《东西方美术的交流》,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8年,第 216页。
3. 1934年开始,赵望云由唐山经八达岭、张家口、大同至内蒙古草原,开西北写生之先河。1943年7月至1945年冬,董希文沿重庆-敦煌-南疆公路(同常书鸿)-敦煌-兰州一路写生。1943年,司徒乔到新疆等西北地区写生。1945和1948年,黄胄跟随其师赵望云到西北写生。还有韩乐然等的西北写生,叶浅予等的西南写生,构成了一个时期的艺术景观。
4.庞薰琹一直在对敦煌进行研究。1978年,在《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即将出版时,他将出版计划延迟一年,前往敦煌考察,圆了自己的“ 敦煌梦” ,也因为这次敦煌之行,对该书进行了最后的修订。
5.〔英〕迈克尔•苏立文著,陈卫和、钱岗南译《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上),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5页。
6.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2页。
7.吴作人百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吴作人年谱 (待定本)》。
8.指善走的骆驼。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毛篇》:“ 驼,性羞。《木兰》篇‘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
9. 1983年“ 孙宗慰遗作展” 研讨会冯法祀发言。
10.朱青生、吴宁主编《当代书画家第一辑吴作人素描基础:新中国画的革命?》, 中国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 58页。
11.《我所走过的艺术道路— — 在一个座谈会上的谈话》,摘自《乡心无限》,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