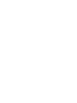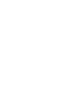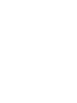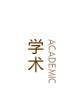庞薰琹的绘画及艺术思想
2011-11-26 08:14:00来源:庞薰琹美术馆点击:4799
作 者:周爱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讲师 博士)
出 版 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探索·探索·再探索— — 纪念庞薰琹先生诞辰105周年艺术展作品集》
出版时间:2011年11月第1版
20世纪初中国艺术如同西方艺术一样进入浩荡的革命潮流之中。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不一样,使得中西艺术喊出的“ 革命” 之声,同声而不同调,中西艺术朝着不同的方向和目标迈进。另外,20世纪也是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交融互渗得到广泛发展的时期,文化交往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并对不同民族和地区的“ 现代” 艺术变革产生了推动作用。东西方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看成是一个“ 结构” 与“ 再结构” 的过程。西方现代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将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艺术“ 结构” 到了西方艺术中,反过来,中国艺术家又通过向西方艺术学习,将一种包容了东方艺术成分的西方艺术“ 再结构” 到东方艺术中去。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艺术都是在这种“ 结构” 与“ 再结构” 的过程中,为自身的艺术发展寻找到新的资源和动力。庞薰琹的人生及艺术探索以这样的时代背景而展开,他的艺术理想与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一生贯穿“ 决澜” 的精神— — 一种矢志不渝勇于开拓的精神以及为理想信念而与苦难抗争的精神,他的卓识远见及执着探索开启了中国现代绘画与现代设计的道路。这里,主要围绕庞薰琹不同时期的绘画创作,探讨他的艺术思想及绘画表现特性以及他的绘画探索对于当今艺术创作的启示性意义。
一
庞薰琹出生于中国江南旧式文人家庭,而他在艺术上的起步成长则是在法国巴黎。1925年,年仅19岁的庞薰琹为追逐内心的艺术梦想只身来到巴黎求学,他爱音乐、诗歌,更爱绘画,巴黎浓重的艺术气息使他沉醉迷恋。他流连于博物馆里的古典绘画,同时也为巴黎正兴起的现代艺术激动不已。丰富璀璨的西方艺术以及浪漫时尚的巴黎都市生活,使一位来自中国乡土的年轻人对艺术及未来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他来到最为火热的现代艺术中心蒙巴尔那斯,在一种自由的充满新鲜活力的氛围中学习和感悟艺术。如他所说:“ 在蒙巴尔那斯的两年活动,所学到的东西,是在任何学校中学不到的。” 西方现代艺术不只是培养了庞薰琹的艺术素养及创作经验,而且教会了他以一双“ 纯真之眼” 和“ 美的相对性” 的意识去认识事物。这双“ 纯真之眼” ,不是停留在外表的对客观物像的直观反映上,而是一种指向内心的、明察内心感受的观看与表现。繁华的巴黎都市使庞薰琹对自己苦难的祖国深深眷念,火热的巴黎艺术更唤取了他对自己民族艺术的依恋,他从常玉、藤田嗣治等人的绘画作品以及巴黎小宫举办的日本绘画展览,体会到东方艺术的独特创造性及其魅力,他还从尼奥太•依尼奥迦的印度舞蹈体会到民族艺术的自信、自尊与自豪。他意识到“ 不是从根上滋长的树,是不会开花结果的” 。
庞薰琹回国之初,参加了“ 苔蒙画会” (“ 苔蒙” 即是法文“ 两个世界” 的音译)。在此期间,庞薰琹创作了《如此巴黎》和《人生哑谜》,这两件作品在形式上明显有着立体主义的构成分割与组合的艺术表现特点,而在形象内容上则是他个人生活体验及经历的反映。这两件作品在视觉上是关联的,他将巴黎与上海的不同生活体验并置在一起。庞薰琹在两种生活体验间游离,此时他还没有完全将两种不同文化空间的生活情景区分开来。如同倪贻德评说的,当他初回国时,还保持着巴黎艺术家的气派— — 黑丝绒的外衣,帽子斜在半边,双手插在裤袋内,长而蓬乱的头发,嘴上老是衔着烟斗,“ 大约他对于巴黎的艺术生活,还是依依难舍吧。” [1]受巴黎现代艺术及其精神的鼓动,年轻的庞薰琹与一些同道者在上海组织成立“ 决澜社” ,力图用“ 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色、线、形交错的世界” 。
庞薰琹在决澜社时期的绘画创作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二次决澜社展览上,庞薰琹作品的题材大多是静物、风景以及忧郁烦闷的青春女性形象,这些作品体现出他的艺术技巧和形式表现的修养。第三次决澜社画展之后,也就是在创作《地之子》和《无题》(压榨机)之后,庞薰琹的艺术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在艺术上不再只是追求纯粹形式的审美趣味,而是将特定的社会思想意识与形式表现相结合,《地之子》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内容。1934年江南大旱,庞薰琹的家乡是重灾区之一,饥饿贫困的农民们流离失所,在死亡线上挣扎,这样的情景加深了他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认识。庞薰琹以一家三口的形象构思了《地之子》,然而,他的作品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如实描绘,而是将悲悯情感以特定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如他所说:“ 我没有把他们画得骨瘦如柴,穿得破破烂烂,相反他们是健康的,我用他们来象征中国。我用孩子来象征当时的中国人民。” 反映在《地之子》中的人性情感实际上贯穿了庞薰琹一生的艺术创作,他总是将苦难与希望并存在一起,用美的光明的形象压制内心剧烈的惨痛。庞薰琹讲到:“ 我决不放弃我的艺术,我要为我的艺术,为悲惨生活中的人民而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代艺术,永远不会重蹈法国或英国艺术发展方向的原因所在。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加人道,更加接近我们人民受苦受难的心。” [2]创作《地之子》之后,庞薰琹不再将艺术置于“ 虚幻” 的梦景之中,他以强烈的人道立场及社会责任意识观察表现现实生活。
日本学者竹内好在评说东方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特点时讲到,东方的现代受到了西方的冲击,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以此意义而言,强调东方的现代与西方无关的本土主义立场是反历史的;同时,东方的现代又不可能在西方意义上完成,直接挪用西方观念的做法只能使自己身处自己的历史之外。对于东方的现代而言,采取自我否定的方式并不意味着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东方的现代只能建立在东方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上。以庞薰琹为代表的决澜社画家们在绘画创作上,尽管选择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但是他们在文化心理上对中国传统艺术价值的认同却是相当一致的。决谰社画家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推崇实际上表达出他们革新中国传统艺术的强烈愿望,他们以反传统的姿态肯定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也就是说,决澜社艺术运动表面上是向外的— — 模仿西方现代艺术,而在潜在的层面上它是向内的— — 挖掘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抱负振兴中国艺术的责任和使命,这是所有积极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决澜社艺术运动兴起之时,傅雷一面为庞薰琹等年轻艺术家的“ 决澜” 精神喝彩,一面大声疾呼,中国艺术的出路应该“ 往深处去!” — — 往历史的深处去,往现实生活的深处去,并以此往艺术的深处去。
二
在组织领导决澜社艺术运动之后,庞薰琹转向了与现代艺术毫无关系的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知识领域,他从中国最为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吸取现代艺术创作的养料。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看似与现代艺术毫无关联,但是从深层的文化生成机制而言,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与现代艺术兴起及发展的历史存在趋同的一面,这些学科研究成果对现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939年秋,庞薰琹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从事传统装饰纹样研究。在那里,他与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历史文化学者相处共事在一起,他的艺术视野伸向了中国古老文化的最深处。在从事传统装饰艺术研究的过程中,庞薰琹受到了考古学、人类学研究理论及方法的熏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学者大多留学国外,这些学者将他们在国外所学的学术方法及观念引入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如傅斯年强调:“ 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他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要“ 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 。历史文化学者重视史料、实证的科学方法以及强调宏观文化视野的研究态度,对庞薰琹从事传统装饰纹样研究产生了影响。
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委派,庞薰琹赴贵州调查少数民族艺术。对庞薰琹而言,这次苗区调查既是一项民族学田野考察,同时也是他在艺术实践上切实走向民间生活的一次体验。在深入到贵州苗寨调查民间艺术时,庞薰琹不仅搜集到了600余件珍贵的民间工艺品,而且在与苗民朝昔相处的日子里,熟悉了苗民的生活习俗,理解了他们的思想情感,这些为他创作以苗民生活为主题的作品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庞薰琹创作的苗民题材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忠实于生活原型,以民族志的方式记录苗民生活内容的作品,如《跳场》、《笙舞》、《背柴》、《车水》、《丧事》、《射牌》、《洗衣》、《苗人畅饮图》等。这些作品重在生活内容的真实再现,描绘苗族特有的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等,准确真实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如他自己说的,在“ 服饰方面,曾尽量保存它原来面目,因为如此,给我不少束缚,也因此,有时不免失去画面的活泼。眼看前人给我们留下许多错误,我不敢欺骗自己,也不愿欺骗后人。于是,像绣花一般把许多花纹照原样的画上了画面。苦闷而又低能!” 这种所谓“ 低能” 的艺术表现,是基于生活真实的表现,与他的艺术理想并不矛盾,而这恰恰是他扎根中国现实的艺术理想的具体反映。还有一类作品是以苗民生活为原型的独立创作,如《背篓》、《盛装》、《橘红时节》、《情话》、《寒林》等,这些作品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性内涵。他在《自剖》(1943年)中曾这样写到:“ 我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所谓的‘读书人’,我虽没有读多少书,却遗传了他们的气质,所以我的画,不免倾向于文学的,似乎是文学的绘画,而不是绘画的绘画。往往粗略于形的描写。我认为‘真’不在于形,而在心。” [3]庞薰琹绘画的文学性,并不是以绘画的形式再现文学的主题和情节,而是指绘画如同诗歌等文学作品一般表现出审美的意境和情感。诗画结合是中国艺术的优良传统之一,庞薰琹创作的充满诗意的绘画作品,正是他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向中国艺术传统回归的一种表现。
这一时期庞薰琹对传统的深入研究也反映在他的线描作品中,他以唐代舞女和贵州苗民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一批精妙绝伦的线描作品。庞薰琹采用了线描的表现方式,但是他又不主张模仿传统线描的手法和形式,他强调线描创作应该与艺术家的个性表现相结合,而不是将生动活现的艺术个性套进已有的线描程式中,使个性受到遏制。
庞薰琹描绘的唐代带舞有着敦煌壁画的飞天神韵,但这些形象又不是对传统形象及线描方法的简单模仿。邓肯、魏格孟和尼奥太•依奥迦的舞蹈在他的内心构成了“ 舞” 的幻象,他要表现“ 舞” 的灵魂和“ 舞” 的民族性格— — 在他的笔下唐代带舞实质是中国艺术的线之舞,他要表现中国绘画的线的灵魂及民族性格。庞薰琹强调研习传统,但不是终止于传统,要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再运用。《卖炭》、《归来》、《收橘》、《持镰》、《母与子》等以苗民生活为原型的线描作品,明显融合了西方写实绘画的造型观念,既强调比例、结构的真实,同时又不失传统线描的韵味及表现魅力。
如同苏立文评价的,如何在中国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使艺术获得再生,不仅要重回传统,找到强有力的民族精神,同时,这种力图恢复和重建的民族艺术精神又必须建立在放眼世界的立场上。抗战时期是庞薰琹艺术探索的沉潜时期,通过对传统装饰纹样的研究及民族民间艺术调查,庞薰琹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及现实社会状况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他将建立中国现代艺术的理想与复兴民族文化精神的愿望复合在一起。他讲到:“ 我总觉得中国的民族在宋代以前,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民族。在想象中,它是一个活泼、勇敢、热情、正直的民族。为什么中国能不屈不挠地长期抗战?就因为在我们的血脉中,幸而还留存着那酷似活泼、勇敢、正直的血液— — 现在我们重建艺术,第一步要恢复这种活泼、勇敢、热情、正直的精神。艺术的园地已一片荒芜,尽量吸收各种文化来培养自己、充实自己是必需的。次一步建设时代的民族文化向世界大同的路上前进。” [4]这种大同的艺术理想,也使得他努力打破各种限制与界限,在中西艺术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工艺美术与绘画创作之间求索与时代与个人艺术理想契合相应的艺术创造。
三
早在巴黎求学时,庞薰琹就意识到“ 美术不只是画几幅画,生活中无处不需要美” ,将艺术与生活结合起来,用艺术实践一种美好的社会生活成为庞薰琹的“ 乌托邦” 梦想。他的梦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实现,他成为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工艺美术学院的重要创建者,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艺美术教育方面。然而,当他满怀激情和信心报效祖国的艺术事业时,却遭遇人生的挫折,他因工艺美术学院办学方向问题而被打成“ 右派”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沉闷压抑时期,他坚守美的艺术信念,用学术研究和绘画创作慰藉苦难的心灵。这一时期,庞薰琹着力于中国古代装饰绘画研究,并从事装饰性的绘画创作,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更为鲜明的艺术思想及绘画创作主张。
1958年到1962年,庞薰琹在人生最为艰难的时期开始写作《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如他自己所说:“ 当时什么写作条件都没有。但是我想到古代装饰画作者,他们何尝有什么创作条件,条件是在劳动中创造的。” 庞薰琹选取了从战国到清代时期有代表性的装饰艺术进行研究,包括帛画、青铜纹饰、画像砖、画像石、石窟壁画与墓室壁画、团扇、屏风画、木刻插图和民间年画等。他勤奋严谨地从事装饰绘画的学术研究,十多次重写汉代部分,彻底推翻三次南北朝的写作内容……。在当时极端狭隘的文艺氛围中,他内心的艺术天地却相当开阔宽广,他大胆突破政治思想的禁锢,以科学态度研究艺术问题,研究艺术形式的特性及规律。
通过古代装饰绘画研究,庞薰琹强调艺术创作应该重视研究工具、材料和工艺手段,将技术表现和思想内容统一起来,应该深入研究艺术“ 变形” 的规律及特性等。庞薰琹认为,在几千年的工艺造物历史中,正是因为工匠们熟悉材料的性质和工具的性能,所以才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表现方法和装饰图案形式。古代艺人从来不会把陶器上的图案硬搬到铜器上去,也不会把铜器上的图案硬搬到瓷器上去,特定的图案形式与特定的工艺材料及制作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工具、材料的限制不仅没有削弱工匠的艺术创造,相反却充分地展现出装饰艺术的特殊性及独特魅力。他指出,技术和思想在装饰艺术创造中同等重要。没有技术,即使思想很高,也只能成为一个思想家,而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一个艺术工作者不单要有高度的思想水平,而且也要有高度的技术水平。研究殷周时期青铜器装饰纹样,使庞薰琹体会到到装饰变形与器物制作技术的关系,“ 变形” 是装饰纹样的一个根本问题,其目的是为了使纹样造型变得更美,是为了符合装饰功能和制作的需要。此外,变形作为一种普遍的艺术表现方法,是运用提炼、概括、省略、夸张、添加,以及象征、联想、拟人化等多种艺术手法,创作出特征明确、形象生动、装饰优美的各种艺术形象。由此他提出,在艺术创作中,写实与变形是辩证统一的,“ 没有不写实的变形,也没有不变形的写实” 。这些研究内容及观点既是对中国古代装饰绘画成就的总结,同时也为现代绘画创作提供了创作方法及理论指导。特别是在一切以“ 阶级斗争” 为纲,以现实主义为文艺创作唯一准则的年代,他坚守艺术的真理,勇于拓展艺术思维和艺术视野,对中国绘画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提出了许多的真知灼见。
庞薰琹将理论研究与绘画创作实践相结合,在六七十年代他创作了大量以花卉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如《74.6.20瓶花》、《紫与白色菊花》、《美人焦》、《瓶花》、《牵牛花》、《玉兰花》、《菊花倒影》等作品。这一时期,庞薰琹对花的描绘有两重深义。一方面,花是人格精神的象征。在人性扭曲的岁月里,他躲在小屋里,将别人遗弃的花草插在瓶中,写生创作作品。他将人性美、善的信念寄托在花卉形象中。另外,这一时期他的绘画作品有着典型的装饰形式特点,这些花卉作品反映出他对绘画装饰性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庞薰琹认为,在汉唐及其以前的装饰艺术中,绘画和装饰并不分家,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古代的工匠艺术家们施匠心于造意,化技巧于笔端,使装饰艺术具有博大深沉的美感及艺术表现力。他以历史例证以及个人的创作实践表明,装饰艺术不只是受制于规则和秩序的艺术,更是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庞薰琹强调笔情与画意相结合,主张表现方法不一而为,灵活多变,他反感将装饰艺术简单而机械地理解为“ 单线平涂” 。[5]他总结装饰绘画“ 求平不是平板,求稳不是死刻,求满不是实结” ,“ 以硬来表现柔,以动来表现静,以重来表现轻,以刚来表现秀” 。对立原则与矛盾统一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具象与抽象,虚与实,动与静,形与神— — 这些关系是构成装饰艺术表现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将这些思想认识生动地表现在自己的绘画作品中。
庞薰琹用他一生的艺术实践表明,在艺术上要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要有顽强的探索精神,许多宝贵的作品是在苦难生活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在庞薰琹的绘画作品中,“ 一条线,一幅纹样,一块颜色,这些都是装饰艺术的简单元素,可是它们在这个时代重新使用时变了。” [6]这种变不只是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变,实质上也是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社会思想观念在改变。他强调在艺术上要有“ 大破大立” 的精神和勇气:破不是把原来的传统抛弃,而是破其凌乱、破其繁琐、破其丑陋、破其单调。立,是要化凌乱为协调,化繁琐为简练,化丑陋为美好,化单调为丰富多彩。他认为,“ 变” 是艺术的常理,“ 不变” 是变的特殊形式。[7]对于外来文化他也持相同的“ 变” 的观念,他说:“ 在我们的传统中,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也从来不生搬别人的东西。我们在艺术上的变,是与西方国家在艺术上的变,性质完全不同。” [8]为什么中西艺术产生不同性质的变呢?民族传统的不同以及现实“ 人民” 需要的不同,决定了中西艺术在相互交流与影响的过程中产生的“ 变” ,不可能重复,不可能以一种模式简单地取代另一种模式。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艺术在相互扩散、彼此碰撞的过程中,既激活各自的艺术生命,也孕育新的艺术创造,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9]庞薰琹的艺术思想浸透着崇尚“ 自然” ,追求普遍和谐的老庄哲学观,他的艺术就是在回根传统文化根性,探索中国艺术现实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开花结果的。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回望庞薰琹的绘画创作及艺术思想,我们认识到,艺术创造的文化根性,既反映为各民族和各地域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应该体现出每位艺术家对自我生活世界的独特理解与表现,惟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在一个共处的历史环境下探讨艺术的多元问题,创造出有中国文化特性的当代艺术。
参考文献:
[1]倪贻德:《决澜社的一群》(1935年),载《倪贻德美术论集》,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年。
[2]苏立文:《回忆庞薰琹》,载《庞薰琹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
[3]庞薰琹《自剖》,载《中央日报》,1943年9月12日。
[4]庞薰琹:《略谈图案》,原载《中央日报》,1944年2月13日。
[5]刘巨德、王玉良:《学贯中西 厚积薄发— — 庞薰琹先生的艺术创作和治学》,载《艺术赤子的求索》,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6]杭间:《手艺的思想》,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7]庞薰琹:《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127页。
[8]庞薰琹:《谈装饰绘画》,载《庞薰琹工艺美术文集》,轻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68页。
[9]汤一介:《东方文化丛书•再版序言》,载《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出 版 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探索·探索·再探索— — 纪念庞薰琹先生诞辰105周年艺术展作品集》
出版时间:2011年11月第1版
20世纪初中国艺术如同西方艺术一样进入浩荡的革命潮流之中。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不一样,使得中西艺术喊出的“ 革命” 之声,同声而不同调,中西艺术朝着不同的方向和目标迈进。另外,20世纪也是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交融互渗得到广泛发展的时期,文化交往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并对不同民族和地区的“ 现代” 艺术变革产生了推动作用。东西方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看成是一个“ 结构” 与“ 再结构” 的过程。西方现代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将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艺术“ 结构” 到了西方艺术中,反过来,中国艺术家又通过向西方艺术学习,将一种包容了东方艺术成分的西方艺术“ 再结构” 到东方艺术中去。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艺术都是在这种“ 结构” 与“ 再结构” 的过程中,为自身的艺术发展寻找到新的资源和动力。庞薰琹的人生及艺术探索以这样的时代背景而展开,他的艺术理想与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一生贯穿“ 决澜” 的精神— — 一种矢志不渝勇于开拓的精神以及为理想信念而与苦难抗争的精神,他的卓识远见及执着探索开启了中国现代绘画与现代设计的道路。这里,主要围绕庞薰琹不同时期的绘画创作,探讨他的艺术思想及绘画表现特性以及他的绘画探索对于当今艺术创作的启示性意义。
一
庞薰琹出生于中国江南旧式文人家庭,而他在艺术上的起步成长则是在法国巴黎。1925年,年仅19岁的庞薰琹为追逐内心的艺术梦想只身来到巴黎求学,他爱音乐、诗歌,更爱绘画,巴黎浓重的艺术气息使他沉醉迷恋。他流连于博物馆里的古典绘画,同时也为巴黎正兴起的现代艺术激动不已。丰富璀璨的西方艺术以及浪漫时尚的巴黎都市生活,使一位来自中国乡土的年轻人对艺术及未来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他来到最为火热的现代艺术中心蒙巴尔那斯,在一种自由的充满新鲜活力的氛围中学习和感悟艺术。如他所说:“ 在蒙巴尔那斯的两年活动,所学到的东西,是在任何学校中学不到的。” 西方现代艺术不只是培养了庞薰琹的艺术素养及创作经验,而且教会了他以一双“ 纯真之眼” 和“ 美的相对性” 的意识去认识事物。这双“ 纯真之眼” ,不是停留在外表的对客观物像的直观反映上,而是一种指向内心的、明察内心感受的观看与表现。繁华的巴黎都市使庞薰琹对自己苦难的祖国深深眷念,火热的巴黎艺术更唤取了他对自己民族艺术的依恋,他从常玉、藤田嗣治等人的绘画作品以及巴黎小宫举办的日本绘画展览,体会到东方艺术的独特创造性及其魅力,他还从尼奥太•依尼奥迦的印度舞蹈体会到民族艺术的自信、自尊与自豪。他意识到“ 不是从根上滋长的树,是不会开花结果的” 。
庞薰琹回国之初,参加了“ 苔蒙画会” (“ 苔蒙” 即是法文“ 两个世界” 的音译)。在此期间,庞薰琹创作了《如此巴黎》和《人生哑谜》,这两件作品在形式上明显有着立体主义的构成分割与组合的艺术表现特点,而在形象内容上则是他个人生活体验及经历的反映。这两件作品在视觉上是关联的,他将巴黎与上海的不同生活体验并置在一起。庞薰琹在两种生活体验间游离,此时他还没有完全将两种不同文化空间的生活情景区分开来。如同倪贻德评说的,当他初回国时,还保持着巴黎艺术家的气派— — 黑丝绒的外衣,帽子斜在半边,双手插在裤袋内,长而蓬乱的头发,嘴上老是衔着烟斗,“ 大约他对于巴黎的艺术生活,还是依依难舍吧。” [1]受巴黎现代艺术及其精神的鼓动,年轻的庞薰琹与一些同道者在上海组织成立“ 决澜社” ,力图用“ 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色、线、形交错的世界” 。
庞薰琹在决澜社时期的绘画创作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二次决澜社展览上,庞薰琹作品的题材大多是静物、风景以及忧郁烦闷的青春女性形象,这些作品体现出他的艺术技巧和形式表现的修养。第三次决澜社画展之后,也就是在创作《地之子》和《无题》(压榨机)之后,庞薰琹的艺术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在艺术上不再只是追求纯粹形式的审美趣味,而是将特定的社会思想意识与形式表现相结合,《地之子》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内容。1934年江南大旱,庞薰琹的家乡是重灾区之一,饥饿贫困的农民们流离失所,在死亡线上挣扎,这样的情景加深了他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认识。庞薰琹以一家三口的形象构思了《地之子》,然而,他的作品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如实描绘,而是将悲悯情感以特定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如他所说:“ 我没有把他们画得骨瘦如柴,穿得破破烂烂,相反他们是健康的,我用他们来象征中国。我用孩子来象征当时的中国人民。” 反映在《地之子》中的人性情感实际上贯穿了庞薰琹一生的艺术创作,他总是将苦难与希望并存在一起,用美的光明的形象压制内心剧烈的惨痛。庞薰琹讲到:“ 我决不放弃我的艺术,我要为我的艺术,为悲惨生活中的人民而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代艺术,永远不会重蹈法国或英国艺术发展方向的原因所在。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加人道,更加接近我们人民受苦受难的心。” [2]创作《地之子》之后,庞薰琹不再将艺术置于“ 虚幻” 的梦景之中,他以强烈的人道立场及社会责任意识观察表现现实生活。
日本学者竹内好在评说东方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特点时讲到,东方的现代受到了西方的冲击,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以此意义而言,强调东方的现代与西方无关的本土主义立场是反历史的;同时,东方的现代又不可能在西方意义上完成,直接挪用西方观念的做法只能使自己身处自己的历史之外。对于东方的现代而言,采取自我否定的方式并不意味着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东方的现代只能建立在东方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上。以庞薰琹为代表的决澜社画家们在绘画创作上,尽管选择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但是他们在文化心理上对中国传统艺术价值的认同却是相当一致的。决谰社画家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推崇实际上表达出他们革新中国传统艺术的强烈愿望,他们以反传统的姿态肯定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也就是说,决澜社艺术运动表面上是向外的— — 模仿西方现代艺术,而在潜在的层面上它是向内的— — 挖掘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抱负振兴中国艺术的责任和使命,这是所有积极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决澜社艺术运动兴起之时,傅雷一面为庞薰琹等年轻艺术家的“ 决澜” 精神喝彩,一面大声疾呼,中国艺术的出路应该“ 往深处去!” — — 往历史的深处去,往现实生活的深处去,并以此往艺术的深处去。
二
在组织领导决澜社艺术运动之后,庞薰琹转向了与现代艺术毫无关系的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知识领域,他从中国最为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吸取现代艺术创作的养料。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看似与现代艺术毫无关联,但是从深层的文化生成机制而言,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与现代艺术兴起及发展的历史存在趋同的一面,这些学科研究成果对现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939年秋,庞薰琹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从事传统装饰纹样研究。在那里,他与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历史文化学者相处共事在一起,他的艺术视野伸向了中国古老文化的最深处。在从事传统装饰艺术研究的过程中,庞薰琹受到了考古学、人类学研究理论及方法的熏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学者大多留学国外,这些学者将他们在国外所学的学术方法及观念引入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如傅斯年强调:“ 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他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要“ 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 。历史文化学者重视史料、实证的科学方法以及强调宏观文化视野的研究态度,对庞薰琹从事传统装饰纹样研究产生了影响。
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委派,庞薰琹赴贵州调查少数民族艺术。对庞薰琹而言,这次苗区调查既是一项民族学田野考察,同时也是他在艺术实践上切实走向民间生活的一次体验。在深入到贵州苗寨调查民间艺术时,庞薰琹不仅搜集到了600余件珍贵的民间工艺品,而且在与苗民朝昔相处的日子里,熟悉了苗民的生活习俗,理解了他们的思想情感,这些为他创作以苗民生活为主题的作品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庞薰琹创作的苗民题材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忠实于生活原型,以民族志的方式记录苗民生活内容的作品,如《跳场》、《笙舞》、《背柴》、《车水》、《丧事》、《射牌》、《洗衣》、《苗人畅饮图》等。这些作品重在生活内容的真实再现,描绘苗族特有的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等,准确真实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如他自己说的,在“ 服饰方面,曾尽量保存它原来面目,因为如此,给我不少束缚,也因此,有时不免失去画面的活泼。眼看前人给我们留下许多错误,我不敢欺骗自己,也不愿欺骗后人。于是,像绣花一般把许多花纹照原样的画上了画面。苦闷而又低能!” 这种所谓“ 低能” 的艺术表现,是基于生活真实的表现,与他的艺术理想并不矛盾,而这恰恰是他扎根中国现实的艺术理想的具体反映。还有一类作品是以苗民生活为原型的独立创作,如《背篓》、《盛装》、《橘红时节》、《情话》、《寒林》等,这些作品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性内涵。他在《自剖》(1943年)中曾这样写到:“ 我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所谓的‘读书人’,我虽没有读多少书,却遗传了他们的气质,所以我的画,不免倾向于文学的,似乎是文学的绘画,而不是绘画的绘画。往往粗略于形的描写。我认为‘真’不在于形,而在心。” [3]庞薰琹绘画的文学性,并不是以绘画的形式再现文学的主题和情节,而是指绘画如同诗歌等文学作品一般表现出审美的意境和情感。诗画结合是中国艺术的优良传统之一,庞薰琹创作的充满诗意的绘画作品,正是他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向中国艺术传统回归的一种表现。
这一时期庞薰琹对传统的深入研究也反映在他的线描作品中,他以唐代舞女和贵州苗民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一批精妙绝伦的线描作品。庞薰琹采用了线描的表现方式,但是他又不主张模仿传统线描的手法和形式,他强调线描创作应该与艺术家的个性表现相结合,而不是将生动活现的艺术个性套进已有的线描程式中,使个性受到遏制。
庞薰琹描绘的唐代带舞有着敦煌壁画的飞天神韵,但这些形象又不是对传统形象及线描方法的简单模仿。邓肯、魏格孟和尼奥太•依奥迦的舞蹈在他的内心构成了“ 舞” 的幻象,他要表现“ 舞” 的灵魂和“ 舞” 的民族性格— — 在他的笔下唐代带舞实质是中国艺术的线之舞,他要表现中国绘画的线的灵魂及民族性格。庞薰琹强调研习传统,但不是终止于传统,要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再运用。《卖炭》、《归来》、《收橘》、《持镰》、《母与子》等以苗民生活为原型的线描作品,明显融合了西方写实绘画的造型观念,既强调比例、结构的真实,同时又不失传统线描的韵味及表现魅力。
如同苏立文评价的,如何在中国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使艺术获得再生,不仅要重回传统,找到强有力的民族精神,同时,这种力图恢复和重建的民族艺术精神又必须建立在放眼世界的立场上。抗战时期是庞薰琹艺术探索的沉潜时期,通过对传统装饰纹样的研究及民族民间艺术调查,庞薰琹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及现实社会状况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他将建立中国现代艺术的理想与复兴民族文化精神的愿望复合在一起。他讲到:“ 我总觉得中国的民族在宋代以前,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民族。在想象中,它是一个活泼、勇敢、热情、正直的民族。为什么中国能不屈不挠地长期抗战?就因为在我们的血脉中,幸而还留存着那酷似活泼、勇敢、正直的血液— — 现在我们重建艺术,第一步要恢复这种活泼、勇敢、热情、正直的精神。艺术的园地已一片荒芜,尽量吸收各种文化来培养自己、充实自己是必需的。次一步建设时代的民族文化向世界大同的路上前进。” [4]这种大同的艺术理想,也使得他努力打破各种限制与界限,在中西艺术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工艺美术与绘画创作之间求索与时代与个人艺术理想契合相应的艺术创造。
三
早在巴黎求学时,庞薰琹就意识到“ 美术不只是画几幅画,生活中无处不需要美” ,将艺术与生活结合起来,用艺术实践一种美好的社会生活成为庞薰琹的“ 乌托邦” 梦想。他的梦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实现,他成为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工艺美术学院的重要创建者,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艺美术教育方面。然而,当他满怀激情和信心报效祖国的艺术事业时,却遭遇人生的挫折,他因工艺美术学院办学方向问题而被打成“ 右派”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沉闷压抑时期,他坚守美的艺术信念,用学术研究和绘画创作慰藉苦难的心灵。这一时期,庞薰琹着力于中国古代装饰绘画研究,并从事装饰性的绘画创作,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更为鲜明的艺术思想及绘画创作主张。
1958年到1962年,庞薰琹在人生最为艰难的时期开始写作《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如他自己所说:“ 当时什么写作条件都没有。但是我想到古代装饰画作者,他们何尝有什么创作条件,条件是在劳动中创造的。” 庞薰琹选取了从战国到清代时期有代表性的装饰艺术进行研究,包括帛画、青铜纹饰、画像砖、画像石、石窟壁画与墓室壁画、团扇、屏风画、木刻插图和民间年画等。他勤奋严谨地从事装饰绘画的学术研究,十多次重写汉代部分,彻底推翻三次南北朝的写作内容……。在当时极端狭隘的文艺氛围中,他内心的艺术天地却相当开阔宽广,他大胆突破政治思想的禁锢,以科学态度研究艺术问题,研究艺术形式的特性及规律。
通过古代装饰绘画研究,庞薰琹强调艺术创作应该重视研究工具、材料和工艺手段,将技术表现和思想内容统一起来,应该深入研究艺术“ 变形” 的规律及特性等。庞薰琹认为,在几千年的工艺造物历史中,正是因为工匠们熟悉材料的性质和工具的性能,所以才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表现方法和装饰图案形式。古代艺人从来不会把陶器上的图案硬搬到铜器上去,也不会把铜器上的图案硬搬到瓷器上去,特定的图案形式与特定的工艺材料及制作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工具、材料的限制不仅没有削弱工匠的艺术创造,相反却充分地展现出装饰艺术的特殊性及独特魅力。他指出,技术和思想在装饰艺术创造中同等重要。没有技术,即使思想很高,也只能成为一个思想家,而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一个艺术工作者不单要有高度的思想水平,而且也要有高度的技术水平。研究殷周时期青铜器装饰纹样,使庞薰琹体会到到装饰变形与器物制作技术的关系,“ 变形” 是装饰纹样的一个根本问题,其目的是为了使纹样造型变得更美,是为了符合装饰功能和制作的需要。此外,变形作为一种普遍的艺术表现方法,是运用提炼、概括、省略、夸张、添加,以及象征、联想、拟人化等多种艺术手法,创作出特征明确、形象生动、装饰优美的各种艺术形象。由此他提出,在艺术创作中,写实与变形是辩证统一的,“ 没有不写实的变形,也没有不变形的写实” 。这些研究内容及观点既是对中国古代装饰绘画成就的总结,同时也为现代绘画创作提供了创作方法及理论指导。特别是在一切以“ 阶级斗争” 为纲,以现实主义为文艺创作唯一准则的年代,他坚守艺术的真理,勇于拓展艺术思维和艺术视野,对中国绘画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提出了许多的真知灼见。
庞薰琹将理论研究与绘画创作实践相结合,在六七十年代他创作了大量以花卉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如《74.6.20瓶花》、《紫与白色菊花》、《美人焦》、《瓶花》、《牵牛花》、《玉兰花》、《菊花倒影》等作品。这一时期,庞薰琹对花的描绘有两重深义。一方面,花是人格精神的象征。在人性扭曲的岁月里,他躲在小屋里,将别人遗弃的花草插在瓶中,写生创作作品。他将人性美、善的信念寄托在花卉形象中。另外,这一时期他的绘画作品有着典型的装饰形式特点,这些花卉作品反映出他对绘画装饰性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庞薰琹认为,在汉唐及其以前的装饰艺术中,绘画和装饰并不分家,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古代的工匠艺术家们施匠心于造意,化技巧于笔端,使装饰艺术具有博大深沉的美感及艺术表现力。他以历史例证以及个人的创作实践表明,装饰艺术不只是受制于规则和秩序的艺术,更是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庞薰琹强调笔情与画意相结合,主张表现方法不一而为,灵活多变,他反感将装饰艺术简单而机械地理解为“ 单线平涂” 。[5]他总结装饰绘画“ 求平不是平板,求稳不是死刻,求满不是实结” ,“ 以硬来表现柔,以动来表现静,以重来表现轻,以刚来表现秀” 。对立原则与矛盾统一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具象与抽象,虚与实,动与静,形与神— — 这些关系是构成装饰艺术表现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将这些思想认识生动地表现在自己的绘画作品中。
庞薰琹用他一生的艺术实践表明,在艺术上要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要有顽强的探索精神,许多宝贵的作品是在苦难生活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在庞薰琹的绘画作品中,“ 一条线,一幅纹样,一块颜色,这些都是装饰艺术的简单元素,可是它们在这个时代重新使用时变了。” [6]这种变不只是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变,实质上也是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社会思想观念在改变。他强调在艺术上要有“ 大破大立” 的精神和勇气:破不是把原来的传统抛弃,而是破其凌乱、破其繁琐、破其丑陋、破其单调。立,是要化凌乱为协调,化繁琐为简练,化丑陋为美好,化单调为丰富多彩。他认为,“ 变” 是艺术的常理,“ 不变” 是变的特殊形式。[7]对于外来文化他也持相同的“ 变” 的观念,他说:“ 在我们的传统中,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也从来不生搬别人的东西。我们在艺术上的变,是与西方国家在艺术上的变,性质完全不同。” [8]为什么中西艺术产生不同性质的变呢?民族传统的不同以及现实“ 人民” 需要的不同,决定了中西艺术在相互交流与影响的过程中产生的“ 变” ,不可能重复,不可能以一种模式简单地取代另一种模式。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艺术在相互扩散、彼此碰撞的过程中,既激活各自的艺术生命,也孕育新的艺术创造,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9]庞薰琹的艺术思想浸透着崇尚“ 自然” ,追求普遍和谐的老庄哲学观,他的艺术就是在回根传统文化根性,探索中国艺术现实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开花结果的。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回望庞薰琹的绘画创作及艺术思想,我们认识到,艺术创造的文化根性,既反映为各民族和各地域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应该体现出每位艺术家对自我生活世界的独特理解与表现,惟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在一个共处的历史环境下探讨艺术的多元问题,创造出有中国文化特性的当代艺术。
参考文献:
[1]倪贻德:《决澜社的一群》(1935年),载《倪贻德美术论集》,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年。
[2]苏立文:《回忆庞薰琹》,载《庞薰琹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
[3]庞薰琹《自剖》,载《中央日报》,1943年9月12日。
[4]庞薰琹:《略谈图案》,原载《中央日报》,1944年2月13日。
[5]刘巨德、王玉良:《学贯中西 厚积薄发— — 庞薰琹先生的艺术创作和治学》,载《艺术赤子的求索》,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6]杭间:《手艺的思想》,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7]庞薰琹:《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127页。
[8]庞薰琹:《谈装饰绘画》,载《庞薰琹工艺美术文集》,轻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68页。
[9]汤一介:《东方文化丛书•再版序言》,载《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