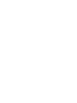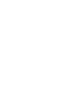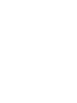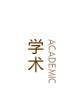海峡两岸黄公望艺术论坛
2011-05-14 02:12:00来源:常熟美术馆点击:8912
活动时间:2011年5月14日
活动地点:北京长白山大酒店
文/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提供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常熟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 海峡两岸黄公望艺术论坛” ,于2011年5月14日在北京隆重举行。此次论坛,也将为今年6月至9月在台北举办“ 山水合璧— — 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 ,拉开了一个序幕。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覃志刚,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董伟,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庆善,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高云,江苏省常熟市市长惠建林等领导参加了活动。
黄公望是元代极为重要的山水画家之一,其与王蒙、倪瓒、吴镇一起被董其昌合称为“ 元季四家” ,他们在山水画上都有着卓越的成就和极高的地位。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是作者于六百多年前的元代为无用师所创作的,三百多年前的清代被焚为两段,其后又分藏于海峡两岸六十余年,可谓历经磨难。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对于黄公望及其《富春山居图》的研究日益增加,有些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此次黄公望艺术论坛,引起了海峡两岸众多专家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研究兴趣,在与会的代表中,有年长资深的老一辈著名美术史论家、文物鉴定专家、艺术院校的教授或研究员,也有新一代出类拔萃的美术史论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高华,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担任领衔主讲。与会代表们围绕着对黄公望历史意义及其影响、黄公望与元代文人画、富春山实景与《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与《剩山图》的真伪辨析、《富春山居图》的表现方式与黄公望《写山水诀》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展开讨论,或激烈争论,或相互补充。
此次论坛的开幕式,由本次论坛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主持,他说:“ 《富春山居图》的悲欢离合记载着传奇的文化史,确如骨肉分离。它的合展,它的重圆是两岸人民的愿望。它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美术作品展览,是同一个血统,同一个文明,根脉相连的需要。‘海峡两岸黄公望艺术论坛’在《富春山居图》合璧的前夕隆重开幕,旨在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忆,进一步沟通心灵,强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推动两岸在文化上深度交流。”
专家论坛分为三场,第一场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吕品田和吴为山主持;第二场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郑工主持;第三场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牛克诚主持。兹将这次论坛所涉及的主要观点和议题综述如下:
一、对黄公望历史意义及其影响的研讨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认为:中国的山水画历史悠久,产生以来也有很多变化,但是元代的山水之变是一个观念性的大变化。所以明代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就讲“ 大痴、黄鹤又一变也” ,就是说黄公望和王蒙山水画所代表的变化,是又一个大的变化,其变有三点,可以通过《富春山居图》来谈一下。一是山水画的功能之变。宋代的山水都是游览和观赏的山水,到了元代就变成了书斋山水,画文人书斋,元代确实出现了不少书斋山水,但是黄公望这件作品《富春山居图》不是书斋山水。也就是说《富春山居图》是他为无用师画的可游可居的山水,并非文人自我标榜的山水,更没有士大夫之气,也并非黄公望自己居住过的书斋环境,而是宽泛的山居景色,是讴歌自在的精神栖居于山光水色之中,表现了一种真正与村夫野老为伍的情怀,这个是黄公望山水的一个变化。第二个是丘壑和空间的变化。黄公望说作画只是一个“ 理” 字最重要,把握了前人对于山水丘壑的图式构造之理的同时,又结合了富春山的实际景观和自己的表现方法。在空间处理上,从《富春山居图》中便可以看出,黄公望讲的阔远主要是针对手卷的,特别是从近处景物间隔中来描写视野的开阔和辽远,这个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个就是笔墨。《富春山居图》充分发挥了用笔,他用线是松动而又灵活的,既描绘了山川形式,江南地貌的清明,又抒发了内心的超远自由。与宋代的山水画相比,其笔势更加连贯,更加混化,关系在若即若离之间,具有一种相对独立的美。可以看出《富春山居图》的笔墨比此前南方画派为主的笔墨不同,它是兼容了北派的因素。有人说北方的山水画派是突出主干线条的,来描写轮廓和凹凸,而南方以董源为代表的画派是不突出主干线条,是用无数的点线来表现。《富春山居图》总体是以点线为主,又不特别强调主干线条的主干作用,显然继承了董源画派的画法。黄公望这种近于自然山水的生成变化之妙,又讲究笔内笔外的种种之美的笔墨表现,是其在研究、继承前人笔墨图式的基础上面对山川自然,与自己的感受加以修正、发展而后形成胸中丘壑。所谓胸中丘壑,并非大自然本身的拷贝,不是画家对景描摹,而是以自然山水作为参照,创造出一个自由的空间世界。事实上,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笔墨的运动在笔内笔外的空间表现中引领丘壑,这也就是以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为代表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杨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指出:邹之麟在《富春山居图》卷《无用师本》的跋文中说:“ 余生平喜画师子久,每对知者论子久画,书中之右军也,圣矣。至若富春山居图,笔端变化鼓舞,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矣。” 把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和王羲之的《兰亭序》联系在一起,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邹之麟把黄公望和《富春山居图》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定了下来,这个定位相当高。我们知道《兰亭序》一直影响到今天,写书的人没有不写《兰亭序》的,至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能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能不能够这样一个定位?这个应该探讨一下。这里就必须要谈到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总的来看,中国山水画的发展经过了三个拐点,或者说是经过了三个变化的关键时期。第一个中国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拐点和变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山水画的体积和空间表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由平面山水变成立体山水。魏晋以后中国画山水画的发展都是画立体山水,包括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仔细看去都是一个个立体山水累积起来了;二是小中见大。离山的距离很近,看不见它的全貌,必须远离才能看到全貌,山水画的这个表现方法就是小中见大,宗炳在《画山水序》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于山水画体积和空间表现的解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画家的贡献,这个拐点过来便是一个新的阶段— — 唐代的青绿山水。第二拐点在唐末到五代时期,这个拐点解决的问题就是山水画的皴法。山水画有了皴法才有笔墨,没有皴法谈不到笔墨。当以线条勾勒为山水的体积和结构的时候,只有笔没有墨,只有连水带墨一起画才是有笔有墨,这就解决了皴法。皴法一解决才出现了宋代水墨山水画的高峰,所以皴法的解决是第二个拐点。第三个拐点就是到了元代。山水画要继续往前推进,要发展,必须在观念上有所变化,这就是要使山水画从客观描绘的形体上解放出来,使笔墨能够凸显它的酣畅淋漓。如邹之麟所说的“ 笔端变化鼓舞” ,这个词相当重要,你看《富春山居图》的“ 笔端” 是鼓舞的、是变化的,让我们除了欣赏画中山水还要欣赏画中笔墨,笔墨的鼓舞直接和人心相联系,它能够把心灵的东西更充分地表达出来。所以《富春山居图》与《千里江山图》有着很大的不同,《富春山居图》在山水结构上是简单的,但是笔墨是畅快的,是淋漓的,所以黄公望就是在这个时代拐点的代表,他把山水画从对自然形态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在笔墨上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发挥它的审美价值。所以邹之麟为什么把黄公望比作王羲之,为什么要把《富春山居图》比作《兰亭序》,就是这个原因。
王耀庭(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指出了《富春山居图》出现以后对于画坛产生很广泛的影响— — 即诸家对于黄公望的学习和诠释。元末明初时期马琬的《春山清霁图》,画面中后方的远山和峰峦的造型,几乎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一个翻版。清代恽寿平说:“ 一峰老人,为胜国诸贤之冠,后惟沈启南(周)得其苍润;董云间(其昌)得其秀润。” 在沈周对于诸贤学习过程当中,惟效倪瓒不似,每临倪瓒的画,他的老师赵同鲁就批评说“ 又过矣,又过矣。” 单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沈周学习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其笔性是比黄公望强烈得多,刚硬得多,实际上沈周以北宗为骨、南宗为面貌的绘画风格,在他临摹的《富春山居图》中得到比较清晰的呈现。明代董其昌在《富春山居图》的题跋里有“ 吾师乎、吾师乎” 几个字,可见其对黄公望绘画的崇尚态度,事实上,在董其昌的心目中仍然是希望有所突破的,其创造的墨韵和抽象式的山水图式,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都得到较为真切的反映。而王时敏的作品《小中见大》,一共有二十四页,二十四页里就有六页是临摹黄公望的作品,在比例上占了四分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黄公望在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地位。王原祁《麓台题画稿》中说:“ 大痴画至富春长卷,笔墨可谓化工。学之者须以神遇,不以迹求。若位置皴染,研求成法,纵与子久行模相似,已落后尘,诸大家不若是拘也。” 可以这样说,王原祁对黄公望的学习已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转化,并不是面对着黄公望的原作来处理的。邹之麟在对黄公望的学习中,作出了进一步的诠释,他说:“ 每得子久画,辄摩挲爱好,如头目脑髓,恨不见其新时,又恐此后日损日少,直欲为渠作一后身,度此一派,此幅拟议,略觉有合。” 金城在其《仿黄公望富春山居》一画中,没有加任何东西,甚至把原画所有的题跋都临了,并且他在画的右上边盖着“ 模范” 这两个字的印,意思是说《富春山居图》的《无用师卷》就是正的。今天是可从多元的宏观角度来评论,当代资深的中国艺术史学者苏利文教授对“ 临、仿” 有了新一番的解释:“ 作画的活动,就像一个钢琴演奏家,演奏名曲一样,我们所欣赏的是他演奏的素质,以及他对(原作的)构图,怎样对原作深刻而微妙的演绎,而不在于构图本身是否新奇。”
二、《富春山居图》与《剩山图》:超越政治的文化合璧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认为:《富春山居图》与《剩山图》的山水合璧,显示出黄公望的山水画在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当中确实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他体会到其中内在心态相当复杂,既有对文化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重新认同的一种喜悦,同时也有一种可以从更广阔的当代空间,重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一种期待。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完全超越地域的限制、超越政治和其他因素,上升到更抽象层面的,即海峡两岸大家内心中的一种文化认同,这可能是两岸交流的一个更重要的价值。
安远远(文化部艺术司文学、美术处处长)指出: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在温总理做了一次很大的传播以后,他从一个艺术史的问题变成了公共文化事件,这个公共文化事件使山水画中“ 江山” 的隐喻,已经不言而喻,非常明白了。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中,江山一直是山水画的一种隐喻,特别是到唐宋以后巨幅的山水出现,达到一种顶峰和极致,给人带来了一种崇高感、崇敬感,而这种崇高感、崇敬感,给予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家、国、天下、社稷江山的意蕴。山水在中国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审美内涵,不光有山水画,还有山水诗。山水是精神,山水的意义比其它文化因素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事实上,一种文化的表现,在一个相对具体的过程中可能不是直接的,特别是文人墨客在表达自己情愫的时候,有特别多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也与自己当时的心情、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等等都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不是南宋的半壁江山,山河破碎,就不会出现一边半角的构图形式,虽说这种构图形式是一种审美的表现,但是它背后的社会问题还是对创作是有影响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可以说是新时代山水画的“ 江山隐喻” 最为典型的代表作品,到了李可染,“ 为祖国山河立传” 已经非常明白地表达了山水画的“ 江山” 意义。在中国文化传承延续里,山水中的“ 江山隐喻” ,从今天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与《剩山图》的两岸合璧,可以看到“ 山水合璧” 这个词有了一种新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回归到我们今天研讨会的本身,回归到我们做艺术史研究和艺术创作过程中来,中国当下的艺术创作似乎是缺少了很多发自于内心、发自于对生活观察提炼的情感和精神。那么我们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对待今天的艺术呢?事实上那个时候绘画的图像传播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人和人之间,人与山水之间的交流哪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对于山水图像的传播就肯定有一种割裂,在今天图像都被泛滥的时候,其实回归到内心、回归到自然本身、回归到学习黄公望在创作《富春山居图》和其它一些山水过程中,这个意义就更加地深远。从山水画到“ 江山隐喻” ,再到感情的抒发,实际上是对山水境界的一种进一步的需要,而两岸共同筹办的“ 山水合璧— — 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 ,也将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情感沟通的一个契机,我想这一次的意义可能会更加深远。
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指出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如何在今天从一种个人的经验转换成国家江山的象征。他认为:当我们说到国家这个词的时候便联系到一种抽象的想象,一幅中国地图,我们在八千米高空看下去的轮廓,这是我们和国家可以联系的一种图像。但是我们看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一种图像,它本来是一种很感性的个人经验,然而在今天却换成了一种国家江山的象征。首先作为物的绘画的命运,从作品的创作、诞生到流传,它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转换。在变迁过程当中,艺术品还经历了一个从私有财产变成公共财产的过程,例如自故宫博物院建立以后,皇帝的私有财产被没收了,随即变成了天下之公共财产。而《富春山居图》从火中被挽救起之后辗转流传,作为一种东西我们会看到离散和相会的意义,《剩山图》和台北故宫收藏的《无用师》版本,这两段就可以想像成它们是孪生兄弟、离合的夫妻,它们再次聚会就被赋于了太多的意义。其次,绘画本身不是一般的东西,它还是承载的图像信息。图像信息的传递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方面是对历史上的一种继承,如《富春山居图》所隐含的董源、巨然等绘画因素;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这个作品完成以后对后来艺术创作的影响,如董其昌和“ 四王” 对于《富春山居图》的学习和演绎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历史当中的图像比物质更加恒久,图像的生命比它作为一个东西的生命更加恒久。另外还可以看到传播方式的改变。大陆拍了很多富春山的实景照片将到台湾同《富春山居图》一起展出,这些东西都是一种传播方式不同的转换。问题是连接这些不同方式的几个方面是靠什么东西连接起来?大概就是人们对山河的感情,对山水的感情,如果是当年黄公望画了两棵白菜,在今天大概不会产生这样的意义。一片水,一重山峦便会使我们想到江山,江山是可游可居的,图像的江山、语言学的江山、政治意义的江山在这个时候完全重合在一起,就从一个人心目中的丘壑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象征,也是一个图像形式的象征。艺术的命运和它的意义,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富春山居图》不只是艺术家们讨论的话题,也不只是艺术史家讨论的话题,它就变成一个可以与其他学科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
三、黄公望与文人画、文人雅集
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对黄公望与元代后期浙西地区文人雅集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他认为黄公望的绘画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黄公望的面貌到现在为止也不是很清楚,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收集资料认真研究。事实上和倪瓒相比,黄公望的资料不是很充分的,而且黄公望的诗和文章也很少,诗大多都是题跋诗,文章也都是题跋,没有一篇真正的文章。黄公望地位已经很高了,但是奇怪的是他死了以后没有人给他写文章,到现在没有看到,也没有墓志铭,没有一个见证。正因为没有很多东西留下来,因此也加深了我们对理解黄公望的困难,这第一点。第二点,黄公望这么一个伟大的画家,他在那个时代一定有他的时代背景,一定跟他的社会环境有关系。事实上,元朝这个时代有它落后的、野蛮的一方面,但是这个时代也有它特殊的、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方面,所以在元代,实际上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得到的发展,而且这个发展是其他所不能相比的。元代有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即实行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正因为这样,南方和北方加强了联系,跟中原加强了联系,这些不但在政治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文化上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南方和北方之间艺术家的交流也是以前没有的,我们对元代历史的重新认识,也就是给元代艺术找一个新的背景。第三点,黄公望当时任浙西宪吏,现在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就是当时的浙西,浙西地区从宋朝以后是京华所在,这个地方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不能说经济发展了文化一定发展,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经济的发展往往带来文化的繁荣,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我做过简单统计,元代有七十个第一流和第二流的画家,其中四十到四十五个在浙西地区,也就是说元代画家里边的大部分第一流和第二流的画家,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浙西地区是元代画家的摇篮,这就是黄公望产生的时代背景、地域背景。这个地方不但出画家,而且出了一批很富有且喜欢文化的人,经常组织一些文人雅集,最有名的就是昆山的“ 玉山雅集” ,顾瑛正是其中的代表。玉山雅集持续大规模的举办,没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文人雅集情况,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一批人,所以在元代浙西地域文化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的,这对于我们研究黄公望及其艺术非常重要。
梁江(中国美术馆副馆长)认为:我们所接触黄公望的史料很少,为什么少?原因是当年他的地位并不高,五十岁以前只不过是一个小吏,五十岁以后也没有怎么发达,然后以卖文和算命为生,还不如现在的画家。另外黄公望还在全真教里边做点传道的事情,就像宗白华先生所讲的人到了那个时候反而平淡了,平淡就能够进入艺术状态,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事实上我们要评判黄公望何以重要这样一个问题,必须把黄公望放在中国山水画史这几个转型期里、放在中国文人画发展的实际语境中去思考,才能探索出相对准确的线索。五代北宋以后,进入元代这个时期,恰好是中国山水画也是文人画的转折点,而在文人画经典图式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元代文人画与宋代文人画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宋代文人画提升的是一种文人余事,苏东坡的绘画就是一种文人墨戏,到了元代不再是文人余事,而是趋于一种较为专业的态势。事实上,在黄公望那里才把文人山水变成一种规范,一种可以传授、可以学习的东西,中国文人画到了文人山水画,变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具有规范性的绘画样式,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我想归结起来就是在元代以前,我们有过唐代的王维,有过宋代的苏轼等文人画的先驱,当时所谓文人画的创作只是文人余事,其技术、素养和表现能力尚不足以表达所有的题材,而且大多数画家都专注于竹、石、梅、兰等。到了后来有一个米氏云山,主要突出了水墨的氤氲,随机性很强,就是这种材质性、随机性的东西很难重复,所以米氏云山不好推广。到了文人山水画兴盛发展出现了“ 元四家” 之后,为我们建立了一种笔墨规范,笔墨技法变成一个丰富的系统,这样文人山水到此就确立了。在元四家当中,黄公望被置于首位,具有正宗流派的意义,不仅因为他是延续了董巨的脉络,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具有文人山水典范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黄公望的时候,看“ 元四家” 的时候,要看到他们在中国文人画,在中国山水画转型期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何以重要,或者说以何重要。
尚辉(《美术》杂志执行主编)认为:我们谈黄公望就离不开谈文人画,谈文人画也离不开谈董其昌的“ 南北宗论” ,事实上在学习文人绘画的过程中,黄公望是比其他诸家更为重要、也更为可学的一个对象。“ 南北宗论” 毫无疑问是董其昌等人在中国画史上提出的最具有理想色彩的理论,其虽然以禅喻画,但实际上是对唐宋以来开始形成的文人画进行了一次理论化的史学梳理和理论升华,“ 南北宗论” 的实质是董其昌对文人画理想的重构。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董其昌画学道路是从黄公望起步而上溯董源,从创作实践逐步上升到南北宗理论的认识,也就是对南北宗论的一种倡导。第二、董其昌确立了黄公望在“ 元季四家” 之中的首位。在元代时候赵孟頫的影响最大,王世贞所谓的“ 元季四家” 是指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四人。董其昌认为赵孟頫不仅是失去了中国文人气节问题,就是他的作品而言也不能放在元四家之中,所以董其昌就把赵孟頫改换为倪瓒,这样一来就把元四家之首的位置让给黄公望。这与他早年推崇和学习黄公望不无关系,在某种意义上黄公望应该是董其昌倡导南宗绘画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黄公望“ 以画为寄” 的人生态度,也更加符合他心目中重构的文人画理想。南北宗论重构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顿悟式的文人画创作心理结构,主要是赋予了文人画以敏锐的艺术直觉和独特的禅宗式的审美启悟,这是文人画理想重构的核心;二是强调以画为寄、以画为乐的创作目的和态度,凸显了绘画所独有的审美愉悦作用和绘画总体的审美价值;三是强调“ 以淡为宗” 的审美意趣,淡既出于自然性情,也离不开人文陶练。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黄公望不仅是董其昌研习画学的启蒙之师,而且在推崇南宗画学的审美观念也给于董其昌深刻的影响,并成为董其昌重构文人画理想重要画家人选和阐释文人画观念的重要依据。南北宗论的意义在于:南北宗论对于文人画理想的重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王维、苏轼等文人画提出、文人画理念的继承与重建,其重构性主要体现在对文人画史的重新认识与重新梳理。因而这种重构是对文人画理念的调整,是对文人画理想的对象化,是对文人画史的重组。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史实,而是通过理论重新构造历史,是带有一种虚构和想象的成份。所以“ 南北宗论” 开辟了师承文人画新的道路,开辟了文人画一个新的发展前景,从中可以看到黄公望对董其昌的影响,以及在南北宗论中的价值和地位。
尚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认为,现在黄公望的诗保存下来有二、三十首,都是在《元诗选》卷十二和卷十四里边,按照一般的记载黄公望是很有诗才的,可是他的诗集没有保存下来,也能够证明黄公望这个人诗的水平应该不太高。从那些诗来看,他的诗在当代绝对不是一流的,能到二流就不错了。可能是《元诗选》的编辑从画里边摘出来的,编辑者是一个挺爱画的人,这个事是一些资料里边有记载的,所以现在保存下来的所谓黄公望的诗,是不是都是真的?我想可能也有假的。
四、从富春山两岸实景到《富春山居图》:中国古代画家的师造化
余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认为:黄公望的山水画常常是以实景为题材,这个与元四家中的其他三家是有所不同,也是比较突出的一点。他的实景往往经过较大的艺术夸张,并不是刻画具体的某一处实景,这在他的立轴山水画当中尤其如此,有的实景直接以道教的活动有关,有一些则是他途径所见之地。比如他的《天池石壁图》,画的是苏州天池山的全景,实际上天池山的高度根本不像画面中那样高耸峻峭,是一片比较平缓的丘陵地貌。其实他这样画体现了他的一种透视的观念,我们过去比较注重是从右向左的栩栩展开,而在《天池石壁图》中则是由下至上的栩栩展开,前山和后山之间相互重叠、交错。另一幅《丹崖玉树图》与《天池石壁图》是非常相近的,而《九峰雪霁图》,是道教隐居炼丹的地方,描绘的是松江的九座道教名山,表达了这位全真教徒的虔敬之心。另外《九珠峰翠图》,也是有实景的,还有《富春大岭图》也是一幅立轴,事实上富春山的两岸没有这样陡峭的高山,完全是他把前后的山峦重叠而成的。再看《富春山居图》,其构图由右向左栩栩展开。在立轴的构图中,由下至上的散点透视造成山体拔高,对实景的描绘比较夸张,而手卷比立轴显然要真实得多。所以黄公望的《富春大岭图》跟富春山的实景有一些距离,而手卷《富春山居图》与富春山的实景更加接近一些。富春山这一地域的长度有100多里,应该是从桐庐的下面一直到富阳,黄公望画了不少与富春山实景有关的作品,有些作品不复存在了,但是在一些元代的文献里可以看到。黄公望作品的题目往往是其所画之地,取其景之大概,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景点,更要记住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的变化。黄公望所绘的《富春山居图》正是他实景山水画的绝顶之作,在此之前,更是为《富春山居图》的创作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综合体现画家的写生能力,这也反映出一个全真教徒晚年的生活— — 来往于大自然的山川之间。
张晴(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主任)论及《富春山居图》和黄公望的师造化时认为:第一,对景写生。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对景写生是非常严谨的,他在创作中非常重视把观照自然山川千变万化的心得和自己的创造融合起来。他的师造化是来自于“ 居” ,在“ 居” 的过程当中再去观察自然、体验自然、深化自然,是一种对景写生后的归纳和主观创造。第二,重视经营位置。黄公望从钱塘江到富春江,再到新安江,这一路绮丽的山山水水让他陶醉其中,《富春山居图》完美的结构布局和空间表现就是他多年的观察与写生的结果,他以平面横移的方式把几百里的山水景色展现在我们眼前,如同一个摄像机的镜头对着已经被剪切过的画面渐渐地移给我们欣赏。在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具体经营位置中,可以看到他把前山与后山之间的关系,安排的是如此自然真切。因此《富春山居图》虽然是黄公望在描绘实景的基础上创作的,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写生,而是在写生的基础上,对富春江两岸的山水形态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取舍。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中经营位置的独道之处在于,他不但考虑到作品整体的构图,也考虑到作品构图与观赏者之间发生的某种心理关系。第三,黄公望在表现语言上的精准。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中把长披麻皴可以说是用到了极致,我在1984年专门到钱塘江和再到新安江一带写生,一个月的时间把那里的山山水水走遍了,我发现富春江两岸的山体只有运用像黄公望这种长披麻皴才能精准地表达出来。事实上,我们从赵孟頫、黄公望、倪瓒的山水画和自然实景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清楚地发现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以各自独到的皴法来表现具体的山水质感,从中获得成功的美学传播。这正是中国古代画家在师造化的过程当中,在各自山水画样式表现和精神追求当中的心灵表现,关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从师造化到云游。黄公望尽管他出生于虞山却不是专门画那里的风景,从他在《富春山居图》的题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从师造化到云游的事实状况,因此黄公望师造化的特征就是“ 云游” 两个字,我们今天要用云游山水之间的心情来品赏《富春山居图》中的云游之意。
五、《富春山居图》的表现方式与黄公望艺术的当代意义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认为,黄公望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黄公望山水画的画法、画理和画格都值得当代中国画家借鉴、学习和反思,此处重点谈一下画格。画格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风格;一个是指格调。黄公望的笔墨风格在元四家中最丰富、最全面,很难用一个字来概括。如果说倪瓒的绘画风格可以用一个“ 简” 字概括,王蒙可以用一个“ 繁” 字概括,吴镇可以用一个“ 湿” 字概括,那么黄公望就不能用一个字概括,因为他是简繁、干湿并用,所以更倾向的画格是指绘画的格调,黄公望山水画的格调是雅、正、清、逸的。同时代的倪云林就说大痴画格超凡俗,指的是他绘画的格调,他还说黄子久之逸脉,就是逸品的脉,董其昌也说黄公望的画“ 神韵飘逸” ,王原祁评价他是“ 高逸” ,并认为是文人画的正传、正宗,但是究竟黄公望的山水画属于“ 神品” 还是“ 逸品” 是有区别的。董其昌说画家以神品为终极,事实上黄公望的画理和倪云林的画理是有所区别的,黄公望注重写真山之形,倪云林注重写胸中逸气,实际上黄公望的山水画是把真山之情与胸中逸气结合起来,形成了雅、正、清、逸的格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高雅的格调?王镛认为黄公望是基于他的深厚的文人修养,寄情山水特别是寄乐于画自黄公望开始,寄乐于画一种超功力的审美态度。倪瓒也说“ 能画大痴黄老子,与人无爱亦无憎” ,就是没有爱憎,不是说黄公望没有感情,而是说他的情感是超凡的、超脱世俗的。当代中国的山水画,很多格调不高,堕入邪、甜、俗、赖的乐趣,可能是因为画家的功利心太重,关心的是画的价格而不是画的格调。其实当代画家应该学习的是黄公望的学习方法,董其昌说:“ 黄子久学北苑,倪云林学北苑,各个不相似” ,所以当代画家学习前人无论是黄公望还是黄宾虹,都应该努力创造自己的面貌。
罗青(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认为: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是中国第一件“ 即兴修补呼应式” 的山水画,并对黄公望这张画做出两点表达和诠释。第一,《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七十九岁比较成熟的作品,是一个水墨写意画,这幅画并不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大制作,至少说依照水墨画的经验,如果经验老道一两个礼拜就可以画完,但为什么要画这么长时间?而且当无用师让他题字的时候,他为何还在题跋里说三、四年没有完备,还要留下来慢慢地画。在黄公望之前,水墨画是有相当的发展,有各式各样的画法,但是没有一个人像黄公望这样清楚地说明,他说画画要从淡墨开始画起,可改可救,他把“ 改” 和“ 救” 当做绘画的一个过程和部分,这是以前没有任何一个画家明确地说出来。事实上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特质,就是他提出了一个不断地修订,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可以互相呼应的一个山水画创作的过程。第二点,富春江既然是这样一个山水,我们用郭熙的方法来画也可以,用范宽的方法来画也可以,用任何方法画都可以,不必要画成黄公望的这个样子,可是黄公望就是很明显的有意识地要继承董源的。但是黄公望画的石头比董源还硬、还多、还大,跟董源的做法并不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发现黄公望引用董源的皴法,与宋朝大量引用典故的风气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仔细看,把黄公望的画放大以后发现他改动的非常明显,这真是所谓进行式的山水,就是永远在进行,这个进行式的山水,事实上黄公望本身就提出了他的理论,他说作画要随机应变,这个画是有生命力的,不断地在改变,你的笔墨之间也要配合重点的改变,使它产生一个复杂的交响,这个交响不但与自己心灵交响,同时也要充满了文化历史感与古人的交响。而这种不断修订的笔墨,到了清代王原祁那儿则发展为一种歪斜交错、来回犹豫不定的程式化图式表现习惯。
陈航(西南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在发言中指出:如果说从宋到元,中国画(尤其山水画)是从“ 形” 向“ 意” 的逐步升华的话,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则是表现这一升华成果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仅从笔墨上看便显示着中国画写意性物化表达的具体成果:其一是笔法的成熟。对于复杂的造化视像,从造型到万物间内在关系,笔法都实现了其最完善的物化层面的表达途径,使笔法成为了中国画语言的基础“ 语法” ,这一“ 语法” 甚至也实现了与中国画特殊工具(如毛笔)的完美结合。笔法具体表现为以线性笔墨为核心的笔的运动方式,即中侧交互、提按交互以及“ 正反弧” 线性交互(线体内外合一的S运动)的共同作用。笔法在绘画主体的艺术探索过程中成为由技入道的起点与途径,成为主体性灵传达的基本载体;其二,“ 达意” 的画境升华促成了“ 草稿之作” 的风尚与新的时代追求。宋代水墨山水画中以淡入浓的绘画基本方法在元代演绎为“ 不经意” 的水墨画稿“ 改本” ,笔墨的疏松错落与绘画主体无拘的精神游走相合一,形成了性灵与笔墨的契合与对应(这种方式的不断推演,最终产生出现代黄宾虹的艺术风格与高度);其三,这种“ 相合一” ,又进一步促成笔墨独立性的自觉,即笔墨表达此物之时亦在表达更为广泛的意义,于是非囿于一形之似,而更贵于不似之境,最终与非囿于一字之似的上乘书法相映照,并从本体上达成一致。于是越界便必然发生,对于书万象皆为“ 帖” ,对于画众书皆达物,也因此善书者每能画,善画者每能书。《富春山居图》所诞生的时代和所传达的艺术指向及其在后世来看所具有的特殊的转型意义,使该作品及其作者黄公望在画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认为,黄公望在通过他很独特的浑厚华滋形象特征来追逐他的内心,通过写生积累,通过他的一种对“ 理” 的追求来展开表现的一个过程。宋元之际,尤其是汉族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进入元代一个异族统治的现实状况中,在那样的处境和空间里所选择的人生立场、价值观与情绪是有很多的关系。确实,在一般情况下,元画的重理似乎是很难把理说清楚的,尤其对于汉族的知识分子而言。但是元画的重趣和后来明代重气的心学思想又是两回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元四家里边确实有相当多的重趣的追求,可为什么黄公望没有选择重趣,仍然是重理呢,这一点对于黄公望作为一个元代的画家,对当时存在问题的思考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黄公望在中年挫折、他对全真教的选择,以及他中年挫折以后开始选择山水画的学习和创作等,可能都跟他对于理的追求有很大的关系。很显然在文人绘画的发展历程当中,黄公望没有选择主观,而是选择相对客观(包含了主观元素的客观)的,所以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主观,这一点可能对我们理解黄公望的创作立场、他的想法、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点。另外,那种由淡到浓、不断地层层往上添加而营造出一个浑厚华滋的山水世界的创作方法,好像是永远处在一个捕捉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仿佛是不断对存在的一些叩问的创作方法。某种意义上说,有点儿像是后来的“ 行动绘画” 的概念。
六、《富春山居图》与《剩山图》的真伪考辨
单国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在发言中认为:《富春山居图》和《剩山图》合璧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当时被毁了以后还没有反映全部的内容,特别是最前边的部分到底发生什么,要了解其首段被烧毁的情况,还需要参照很多临摹本。《子明卷》和沈周临本,中间部分与《无用师卷》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而前面的部分就不一样了。《子明卷》的最前面画了一个小幅,然后是一个平台,跨过了河,再过来的山就是现在的《剩山图》这一部分。沈周临本基本跟《子明卷》差不多,前面是一个小幅,跨河是一个桥,平台过来就是一个高峰,就是现在看到的《剩山图》的这部分。最后结尾部分有很大的不同,《无用师卷》的最后是一片水域,《子明卷》就不是了,平滩上生出许多小树,而沈周临本最后也少了很多水域,大概是背临时简化了。事实上,经过分析《子明卷》和沈周临本都是根据《无用师卷》临摹的,那为什么前面不是“ 平沙五尺” ,说法不一样,甚至认为《子明卷》和沈周临本不是临摹现在的《无用师卷》,另外还有本子,这个参考有没有,到底前边那部分画的是什么,现在我就想解释一下,沈周这个本肯定临了是《无用师卷》之本,因为有沈周的题跋,谈到了收到以后又丢了,自己临的本子上也有题跋,因此,沈周临的绝对不会是另外一个本子。《子明卷》的起首,其长度到《剩山图》那个位置,跟《剩山图》的尺寸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它也有52厘米左右。按照乾隆时候的尺寸来算,一个尺相当于20厘米,被烧掉的“ 五尺” 可折算为117厘米,这还差了57厘米,这个差别的已经不是很大了。《子明卷》作为一个临摹本,很有可能把画面中很多平沙、很多空旷的地方给压缩了,而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于沈周临本中。从“ 尺寸” 跟“ 平沙” 这两个因素来分析,我们可以证明《子明卷》、沈周临本其原本就是现在的《无用师卷》之本,其中的部分就是被烧的部分。另外,就是很多著作记载《富春山居图》的时候,后面题跋的人不一样,一会儿这个人出来了,一会儿这个人又没有了,说明《富春山居图》有好几个本子,当然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再研究,但这不影响《子明卷》、沈周临本和《无用师卷》三本之间直接关系,我们根据《子明卷》和沈周临本同样可以了解到《富春山居图》的全貌。
许洪流(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在发言中对《剩山图》的真实性做出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并指出了关于鉴定《剩山图》的三个问题:一、《富春山居图》毁损了什么?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富春山居图》原来的长度。《无用师卷》目前总长度是636.9厘米,为完整的六张纸,每张纸的长度基本接近,平均长度是106.15厘米左右。参照恽寿平先生的记载烧焦部分还有两张纸,按照常理手卷和画卷一张纸不会特别短,当初烧毁之前的《富春山居图》的总长度应该是849.2厘米,即《无用师卷》的636.9厘米,再加上前面两张纸的长度。其次是关于烧毁的内容,最为重要的线索就是恽寿平《南田画跋》的记载:“ ……焚其起手一段。余因问卿从子问其起手处,写城楼睥睨一角,却作平沙。秃锋为之,极苍莽之致。平沙盖写富春江口出钱塘景也。自平沙五尺余以后,方起峰峦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余耳。” 已经烧毁的部分,一大块在浙江博物馆收藏的《剩山图》,那边是《无用师卷》的开始,在《剩山图》和《无用师卷》的衔接处就是“ 平沙五尺余” 。还有《富春山居图》原来的高度是多少。《无用师卷》的高度是33厘米,《剩山图》的高度是31.8厘米,问题是两图高度相差1.2厘米,《无用师卷》的高度是否少于未烧毁时的《富春山居图》?比较可能的原因是烧毁的时候手卷两端也烧焦了,《无用师卷》装裱的时候上下被裁切过,只不过上下被裁掉的内容没有《剩山图》多,这是比较正站得住脚一个解释。二、《剩山图》真伪的关键— — “ 吴之矩” 骑缝章。关于《剩山图》和《无用师卷》的骑缝章,是对它真伪鉴定的一个关键,我们来看一下吴其贞的《书画记》中说到的内容:“ ……今将前烧焦一纸揭下,仍五纸长三丈……为丹阳张范我所得……其图揭下烧焦纸尚存尺五六寸……今为予所得,名为《剩山图》。” 目前我们看到《剩山图》这个图章有一些倾斜,而《无用师卷》的图章也是略微有一点倾斜,并且倾斜度和《剩山图》完全在一条线上,假如说是后人买到了《剩山图》之后,没有《无用师卷》旁边做对子肯定不会对好,因此可以推测吴其贞在得到《剩山图》之前这个骑缝章就盖好了。三,质疑《剩山图》的“ 八不合” 成立吗?所谓“ 八不合” ,即1、纸色不一,2、墨色不同,3、山不相连,4、皴法不对,5、苔点不类,6、树木不同,7、小屋相异,8、水不能连。许洪流通过对《剩山图》、《无用师卷》、《子明卷》等不同本的具体内容进行了严谨的比较分析,认为对《剩山图》“ 八不合” 的质疑是不能成立的。
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首先回顾了《富春山居图》三个阶段的真伪论辩,第一阶段是乾隆皇帝鉴定《子明卷》为黄公望的真迹,而《无用师卷》被确定为假的;第二阶段是近几十年中,海峡两岸对已经确认为黄公望真本的《无用师卷》提出质疑,并对《富春山居图》火焚事情产生疑问;第三个阶段最终的结论是支持了《无用师卷》的真实性。另外,任平还说明了鉴定《富春山居图》应该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从乾隆皇帝鉴定的事情得出来的一个体会,就是鉴定一定要用作品说话,要以文献为依据,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要以某些权威尤其是帝王的权威为准绳。因为一旦掺入了政治因素,掺入了某种权威因素,往往判断就会失效。第二,美术作品真伪的考辨,不能光是注重于文字的著录,更要重视图像本身。图像与文字是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他们各自在鉴定过程当中各有优劣,各有长短,而美术作品的鉴定包括所有的细节、纸张的质量、笔墨、印章、装裱、时代特征、以及所有的题跋等。第三,图像考证在美术作品的鉴定当中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文字与图像的结合是今后要特别注意的。第四点,联系到《富春山居图》真伪的论辩,把它跟《兰亭》论辩一比较,就可以发现这两个论辩是中国文化史上面两大个案,同样都是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认为两岸所藏的《富春山居图》和《剩山图》都是真迹,二者的颜色是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才是对的,一个在故宫里保存得好,一个在民间保存得不好,在民间保存得不好就会发暗,如果《剩山图》发亮就错了,《富春山居图》在故宫保存得好一点就亮一点。
七、关于《写山水诀》、《快雪时晴图》、《富春山居图》画风及其他的研讨
李福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在关于黄公望《写山水诀》的绘画思想的发言中指出:黄公望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南画发展的过程中,黄公望引领文人画走向全面成熟,同时也为明清南画开辟了一个新的画格。黄公望提出的“ 作画大要,去邪、甜、俗、赖” 四个字,这不仅是黄公望的绘画主张,也是南画画格的精神或者是南画的指导原则,如果把这四个字的理解和解释都搞得很透彻,无疑是解开南画秘密的一个关键。“ 甜” 的对应面就是苦,是苦涩,艺术品的苦涩可以使观众感到有嚼头,有味道,可以回味。艺术家们如何避免作品的“ 甜” ,怎么样去“ 甜” ,李福顺认为只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才能够体会,才能够做到。“ 邪” ,就是有悖常理,扭曲变态,如元代饶自然《绘宗十二忌》中说:“ 一、布置迫塞;二、远近不分;三、山无气脉;四 、水无源流;五、境无夷险;六、路无出入;七、石止一面;八、树少四枝;九、人物伛偻;十、楼阁错杂;十一、滃淡失宜;十二、点染无法。” 等等,总之是失去了和谐,违背对立统一。“ 俗” ,画家最忌讳俗。黄庭坚曾经说过“ 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入耳。” 黄庭坚讲的是书法,书法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就为不俗,画如果过于简单,没有什么可回旋的余地,没有什么可捉摸的,平平淡淡就是俗了。“ 赖” ,用来形容人的一种心理状态,作为画而言就是不耐看、不吸引人。赖的反面是好,好就是要吸引人,要吸引人的作品就要有新意,无论内容或者形式,都是新颖的、耐看的。好的画要合理,所以黄公望说作画只是个“ 理” 字最要紧,《富春山居图》就是黄公望艺术主张最好的范本,是典型的南画。最后李福顺认为,黄公望提出的“ 邪、甜、俗、赖” 四个字,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王连起(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在发言中谈及黄公望《快雪时晴图》时认为:乾隆皇帝喜欢最好的三件书法叫《三希》,第一希就是《快雪时晴帖》,《快雪时晴帖》是王羲之65岁时所书,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当年赵子昂是见过的,真迹后边还有赵孟頫的题跋。于是他就放大临写了“ 快雪时晴” 四个大字送给黄公望,赵子昂临书是以貌取神,不像清代的碑学家们按图索骥。后来赵孟頫送给黄公望的“ 快雪时晴” 四个大字,就被装裱在黄公望《快雪时晴图》的最前面,而《快雪时晴图》,从画法上绝对是黄公望的真迹。事实上,黄公望是赵孟頫自己承认的学生,黄公望的绘画是通过赵孟頫改造过的董源、巨然的画法,这一点应该有一个交待。赵孟頫在于他把董源、巨然、李成、郭熙等都转变为文人的笔法,相传于不同的人,学习董源、巨然的有元四家特别是黄公望和王蒙,学习李成、郭熙的有唐棣、曹知白、朱德润等,在他们存世的画作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另外,王连起还提到董其昌南北宗问题,认为董其昌对赵孟頫是存有偏见的,在他的南宗系统里没有赵孟頫,北宗系统里也没有赵孟頫,但是当他提到元四家的时候,认为元四家都是有赖于赵孟頫提高绘画品格的,事实上还是承认赵孟頫对元四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王连起还说,元四家中吴镇是用墨见长,王蒙构图可繁可简,多种多样,倪云林只有简,王蒙会很多套路,而倪云林就是三拳加一腿,练来练去就是那几招,但是因为笔墨好,百看不厌,这一点也是他的特殊。而黄公望是兼而有之的。现在看到的黄公望的作品真迹,像《天池石壁》、《九峰雪霁》、《快雪时晴》等从画法、皴法变化多端,可见黄公望技法、面貌是很丰富的。黄公望的浅绛山水,就是经过赵孟頫改造的董源、巨然这类绘画,其《天池石壁》、《丹崖玉树》这种画法对清初“ 四王” 影响很大,而《九峰雪霁》、《快雪时晴》则更为精炼,所以黄公望确实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事实上他的《富春山居图》、《天池石壁》,已经让明清时期的文人画跳不出来了,由此可见,他在绘画史上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认为:黄公望的原籍是江苏常熟人,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不少文献都有记载。关于吴之矩,吴问卿的问题,事实上他不叫吴问卿,叫吴冏卿。为什么说吴冏卿对而吴问卿错了,因为名和字是相配的。邹之麟的题跋是问卿,应该是误写,还有一些人是根据邹之麟的记载也写问卿,所以冏卿是对的。再者“ 冏” 和“ 问” 差不多,有时候写错了,自己也默认了。对于火烧的问题陈传席认为是吴冏卿造的谣言,邹之麟的题跋没有提到,有可能是吴冏卿的侄子把《富春山居图》分成了三段卖钱了。另外,陈传席还认为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是董源、巨然的画风,而黄公望学习的是赵孟頫变化了的董源、巨然。赵孟頫把董源、巨然的皴擦变化成书法线条,像《鹊华秋色图》一样,后人看到这张画就认为董源、巨然就是这种画法,沈周也认为这是董源、巨然的画法。有人说《富春山居图》是学董源、巨然的,其实是学赵孟頫的,是通过赵孟頫学董源、巨然的。
(2011年5月21日李月林整理)
活动地点:北京长白山大酒店
文/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提供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常熟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 海峡两岸黄公望艺术论坛” ,于2011年5月14日在北京隆重举行。此次论坛,也将为今年6月至9月在台北举办“ 山水合璧— — 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 ,拉开了一个序幕。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覃志刚,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董伟,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庆善,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高云,江苏省常熟市市长惠建林等领导参加了活动。
黄公望是元代极为重要的山水画家之一,其与王蒙、倪瓒、吴镇一起被董其昌合称为“ 元季四家” ,他们在山水画上都有着卓越的成就和极高的地位。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是作者于六百多年前的元代为无用师所创作的,三百多年前的清代被焚为两段,其后又分藏于海峡两岸六十余年,可谓历经磨难。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对于黄公望及其《富春山居图》的研究日益增加,有些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此次黄公望艺术论坛,引起了海峡两岸众多专家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研究兴趣,在与会的代表中,有年长资深的老一辈著名美术史论家、文物鉴定专家、艺术院校的教授或研究员,也有新一代出类拔萃的美术史论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高华,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担任领衔主讲。与会代表们围绕着对黄公望历史意义及其影响、黄公望与元代文人画、富春山实景与《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与《剩山图》的真伪辨析、《富春山居图》的表现方式与黄公望《写山水诀》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展开讨论,或激烈争论,或相互补充。
此次论坛的开幕式,由本次论坛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主持,他说:“ 《富春山居图》的悲欢离合记载着传奇的文化史,确如骨肉分离。它的合展,它的重圆是两岸人民的愿望。它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美术作品展览,是同一个血统,同一个文明,根脉相连的需要。‘海峡两岸黄公望艺术论坛’在《富春山居图》合璧的前夕隆重开幕,旨在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忆,进一步沟通心灵,强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推动两岸在文化上深度交流。”
专家论坛分为三场,第一场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吕品田和吴为山主持;第二场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郑工主持;第三场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牛克诚主持。兹将这次论坛所涉及的主要观点和议题综述如下:
一、对黄公望历史意义及其影响的研讨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认为:中国的山水画历史悠久,产生以来也有很多变化,但是元代的山水之变是一个观念性的大变化。所以明代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就讲“ 大痴、黄鹤又一变也” ,就是说黄公望和王蒙山水画所代表的变化,是又一个大的变化,其变有三点,可以通过《富春山居图》来谈一下。一是山水画的功能之变。宋代的山水都是游览和观赏的山水,到了元代就变成了书斋山水,画文人书斋,元代确实出现了不少书斋山水,但是黄公望这件作品《富春山居图》不是书斋山水。也就是说《富春山居图》是他为无用师画的可游可居的山水,并非文人自我标榜的山水,更没有士大夫之气,也并非黄公望自己居住过的书斋环境,而是宽泛的山居景色,是讴歌自在的精神栖居于山光水色之中,表现了一种真正与村夫野老为伍的情怀,这个是黄公望山水的一个变化。第二个是丘壑和空间的变化。黄公望说作画只是一个“ 理” 字最重要,把握了前人对于山水丘壑的图式构造之理的同时,又结合了富春山的实际景观和自己的表现方法。在空间处理上,从《富春山居图》中便可以看出,黄公望讲的阔远主要是针对手卷的,特别是从近处景物间隔中来描写视野的开阔和辽远,这个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个就是笔墨。《富春山居图》充分发挥了用笔,他用线是松动而又灵活的,既描绘了山川形式,江南地貌的清明,又抒发了内心的超远自由。与宋代的山水画相比,其笔势更加连贯,更加混化,关系在若即若离之间,具有一种相对独立的美。可以看出《富春山居图》的笔墨比此前南方画派为主的笔墨不同,它是兼容了北派的因素。有人说北方的山水画派是突出主干线条的,来描写轮廓和凹凸,而南方以董源为代表的画派是不突出主干线条,是用无数的点线来表现。《富春山居图》总体是以点线为主,又不特别强调主干线条的主干作用,显然继承了董源画派的画法。黄公望这种近于自然山水的生成变化之妙,又讲究笔内笔外的种种之美的笔墨表现,是其在研究、继承前人笔墨图式的基础上面对山川自然,与自己的感受加以修正、发展而后形成胸中丘壑。所谓胸中丘壑,并非大自然本身的拷贝,不是画家对景描摹,而是以自然山水作为参照,创造出一个自由的空间世界。事实上,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笔墨的运动在笔内笔外的空间表现中引领丘壑,这也就是以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为代表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杨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指出:邹之麟在《富春山居图》卷《无用师本》的跋文中说:“ 余生平喜画师子久,每对知者论子久画,书中之右军也,圣矣。至若富春山居图,笔端变化鼓舞,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矣。” 把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和王羲之的《兰亭序》联系在一起,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邹之麟把黄公望和《富春山居图》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定了下来,这个定位相当高。我们知道《兰亭序》一直影响到今天,写书的人没有不写《兰亭序》的,至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能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能不能够这样一个定位?这个应该探讨一下。这里就必须要谈到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总的来看,中国山水画的发展经过了三个拐点,或者说是经过了三个变化的关键时期。第一个中国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拐点和变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山水画的体积和空间表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由平面山水变成立体山水。魏晋以后中国画山水画的发展都是画立体山水,包括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仔细看去都是一个个立体山水累积起来了;二是小中见大。离山的距离很近,看不见它的全貌,必须远离才能看到全貌,山水画的这个表现方法就是小中见大,宗炳在《画山水序》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于山水画体积和空间表现的解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画家的贡献,这个拐点过来便是一个新的阶段— — 唐代的青绿山水。第二拐点在唐末到五代时期,这个拐点解决的问题就是山水画的皴法。山水画有了皴法才有笔墨,没有皴法谈不到笔墨。当以线条勾勒为山水的体积和结构的时候,只有笔没有墨,只有连水带墨一起画才是有笔有墨,这就解决了皴法。皴法一解决才出现了宋代水墨山水画的高峰,所以皴法的解决是第二个拐点。第三个拐点就是到了元代。山水画要继续往前推进,要发展,必须在观念上有所变化,这就是要使山水画从客观描绘的形体上解放出来,使笔墨能够凸显它的酣畅淋漓。如邹之麟所说的“ 笔端变化鼓舞” ,这个词相当重要,你看《富春山居图》的“ 笔端” 是鼓舞的、是变化的,让我们除了欣赏画中山水还要欣赏画中笔墨,笔墨的鼓舞直接和人心相联系,它能够把心灵的东西更充分地表达出来。所以《富春山居图》与《千里江山图》有着很大的不同,《富春山居图》在山水结构上是简单的,但是笔墨是畅快的,是淋漓的,所以黄公望就是在这个时代拐点的代表,他把山水画从对自然形态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在笔墨上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发挥它的审美价值。所以邹之麟为什么把黄公望比作王羲之,为什么要把《富春山居图》比作《兰亭序》,就是这个原因。
王耀庭(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指出了《富春山居图》出现以后对于画坛产生很广泛的影响— — 即诸家对于黄公望的学习和诠释。元末明初时期马琬的《春山清霁图》,画面中后方的远山和峰峦的造型,几乎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一个翻版。清代恽寿平说:“ 一峰老人,为胜国诸贤之冠,后惟沈启南(周)得其苍润;董云间(其昌)得其秀润。” 在沈周对于诸贤学习过程当中,惟效倪瓒不似,每临倪瓒的画,他的老师赵同鲁就批评说“ 又过矣,又过矣。” 单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沈周学习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其笔性是比黄公望强烈得多,刚硬得多,实际上沈周以北宗为骨、南宗为面貌的绘画风格,在他临摹的《富春山居图》中得到比较清晰的呈现。明代董其昌在《富春山居图》的题跋里有“ 吾师乎、吾师乎” 几个字,可见其对黄公望绘画的崇尚态度,事实上,在董其昌的心目中仍然是希望有所突破的,其创造的墨韵和抽象式的山水图式,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都得到较为真切的反映。而王时敏的作品《小中见大》,一共有二十四页,二十四页里就有六页是临摹黄公望的作品,在比例上占了四分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黄公望在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地位。王原祁《麓台题画稿》中说:“ 大痴画至富春长卷,笔墨可谓化工。学之者须以神遇,不以迹求。若位置皴染,研求成法,纵与子久行模相似,已落后尘,诸大家不若是拘也。” 可以这样说,王原祁对黄公望的学习已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转化,并不是面对着黄公望的原作来处理的。邹之麟在对黄公望的学习中,作出了进一步的诠释,他说:“ 每得子久画,辄摩挲爱好,如头目脑髓,恨不见其新时,又恐此后日损日少,直欲为渠作一后身,度此一派,此幅拟议,略觉有合。” 金城在其《仿黄公望富春山居》一画中,没有加任何东西,甚至把原画所有的题跋都临了,并且他在画的右上边盖着“ 模范” 这两个字的印,意思是说《富春山居图》的《无用师卷》就是正的。今天是可从多元的宏观角度来评论,当代资深的中国艺术史学者苏利文教授对“ 临、仿” 有了新一番的解释:“ 作画的活动,就像一个钢琴演奏家,演奏名曲一样,我们所欣赏的是他演奏的素质,以及他对(原作的)构图,怎样对原作深刻而微妙的演绎,而不在于构图本身是否新奇。”
二、《富春山居图》与《剩山图》:超越政治的文化合璧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认为:《富春山居图》与《剩山图》的山水合璧,显示出黄公望的山水画在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当中确实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他体会到其中内在心态相当复杂,既有对文化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重新认同的一种喜悦,同时也有一种可以从更广阔的当代空间,重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一种期待。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完全超越地域的限制、超越政治和其他因素,上升到更抽象层面的,即海峡两岸大家内心中的一种文化认同,这可能是两岸交流的一个更重要的价值。
安远远(文化部艺术司文学、美术处处长)指出: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在温总理做了一次很大的传播以后,他从一个艺术史的问题变成了公共文化事件,这个公共文化事件使山水画中“ 江山” 的隐喻,已经不言而喻,非常明白了。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中,江山一直是山水画的一种隐喻,特别是到唐宋以后巨幅的山水出现,达到一种顶峰和极致,给人带来了一种崇高感、崇敬感,而这种崇高感、崇敬感,给予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家、国、天下、社稷江山的意蕴。山水在中国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审美内涵,不光有山水画,还有山水诗。山水是精神,山水的意义比其它文化因素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事实上,一种文化的表现,在一个相对具体的过程中可能不是直接的,特别是文人墨客在表达自己情愫的时候,有特别多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也与自己当时的心情、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等等都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不是南宋的半壁江山,山河破碎,就不会出现一边半角的构图形式,虽说这种构图形式是一种审美的表现,但是它背后的社会问题还是对创作是有影响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可以说是新时代山水画的“ 江山隐喻” 最为典型的代表作品,到了李可染,“ 为祖国山河立传” 已经非常明白地表达了山水画的“ 江山” 意义。在中国文化传承延续里,山水中的“ 江山隐喻” ,从今天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与《剩山图》的两岸合璧,可以看到“ 山水合璧” 这个词有了一种新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回归到我们今天研讨会的本身,回归到我们做艺术史研究和艺术创作过程中来,中国当下的艺术创作似乎是缺少了很多发自于内心、发自于对生活观察提炼的情感和精神。那么我们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对待今天的艺术呢?事实上那个时候绘画的图像传播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人和人之间,人与山水之间的交流哪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对于山水图像的传播就肯定有一种割裂,在今天图像都被泛滥的时候,其实回归到内心、回归到自然本身、回归到学习黄公望在创作《富春山居图》和其它一些山水过程中,这个意义就更加地深远。从山水画到“ 江山隐喻” ,再到感情的抒发,实际上是对山水境界的一种进一步的需要,而两岸共同筹办的“ 山水合璧— — 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 ,也将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情感沟通的一个契机,我想这一次的意义可能会更加深远。
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指出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如何在今天从一种个人的经验转换成国家江山的象征。他认为:当我们说到国家这个词的时候便联系到一种抽象的想象,一幅中国地图,我们在八千米高空看下去的轮廓,这是我们和国家可以联系的一种图像。但是我们看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一种图像,它本来是一种很感性的个人经验,然而在今天却换成了一种国家江山的象征。首先作为物的绘画的命运,从作品的创作、诞生到流传,它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转换。在变迁过程当中,艺术品还经历了一个从私有财产变成公共财产的过程,例如自故宫博物院建立以后,皇帝的私有财产被没收了,随即变成了天下之公共财产。而《富春山居图》从火中被挽救起之后辗转流传,作为一种东西我们会看到离散和相会的意义,《剩山图》和台北故宫收藏的《无用师》版本,这两段就可以想像成它们是孪生兄弟、离合的夫妻,它们再次聚会就被赋于了太多的意义。其次,绘画本身不是一般的东西,它还是承载的图像信息。图像信息的传递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方面是对历史上的一种继承,如《富春山居图》所隐含的董源、巨然等绘画因素;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这个作品完成以后对后来艺术创作的影响,如董其昌和“ 四王” 对于《富春山居图》的学习和演绎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历史当中的图像比物质更加恒久,图像的生命比它作为一个东西的生命更加恒久。另外还可以看到传播方式的改变。大陆拍了很多富春山的实景照片将到台湾同《富春山居图》一起展出,这些东西都是一种传播方式不同的转换。问题是连接这些不同方式的几个方面是靠什么东西连接起来?大概就是人们对山河的感情,对山水的感情,如果是当年黄公望画了两棵白菜,在今天大概不会产生这样的意义。一片水,一重山峦便会使我们想到江山,江山是可游可居的,图像的江山、语言学的江山、政治意义的江山在这个时候完全重合在一起,就从一个人心目中的丘壑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象征,也是一个图像形式的象征。艺术的命运和它的意义,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富春山居图》不只是艺术家们讨论的话题,也不只是艺术史家讨论的话题,它就变成一个可以与其他学科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
三、黄公望与文人画、文人雅集
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对黄公望与元代后期浙西地区文人雅集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他认为黄公望的绘画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黄公望的面貌到现在为止也不是很清楚,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收集资料认真研究。事实上和倪瓒相比,黄公望的资料不是很充分的,而且黄公望的诗和文章也很少,诗大多都是题跋诗,文章也都是题跋,没有一篇真正的文章。黄公望地位已经很高了,但是奇怪的是他死了以后没有人给他写文章,到现在没有看到,也没有墓志铭,没有一个见证。正因为没有很多东西留下来,因此也加深了我们对理解黄公望的困难,这第一点。第二点,黄公望这么一个伟大的画家,他在那个时代一定有他的时代背景,一定跟他的社会环境有关系。事实上,元朝这个时代有它落后的、野蛮的一方面,但是这个时代也有它特殊的、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方面,所以在元代,实际上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得到的发展,而且这个发展是其他所不能相比的。元代有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即实行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正因为这样,南方和北方加强了联系,跟中原加强了联系,这些不但在政治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文化上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南方和北方之间艺术家的交流也是以前没有的,我们对元代历史的重新认识,也就是给元代艺术找一个新的背景。第三点,黄公望当时任浙西宪吏,现在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就是当时的浙西,浙西地区从宋朝以后是京华所在,这个地方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不能说经济发展了文化一定发展,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经济的发展往往带来文化的繁荣,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我做过简单统计,元代有七十个第一流和第二流的画家,其中四十到四十五个在浙西地区,也就是说元代画家里边的大部分第一流和第二流的画家,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浙西地区是元代画家的摇篮,这就是黄公望产生的时代背景、地域背景。这个地方不但出画家,而且出了一批很富有且喜欢文化的人,经常组织一些文人雅集,最有名的就是昆山的“ 玉山雅集” ,顾瑛正是其中的代表。玉山雅集持续大规模的举办,没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文人雅集情况,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一批人,所以在元代浙西地域文化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的,这对于我们研究黄公望及其艺术非常重要。
梁江(中国美术馆副馆长)认为:我们所接触黄公望的史料很少,为什么少?原因是当年他的地位并不高,五十岁以前只不过是一个小吏,五十岁以后也没有怎么发达,然后以卖文和算命为生,还不如现在的画家。另外黄公望还在全真教里边做点传道的事情,就像宗白华先生所讲的人到了那个时候反而平淡了,平淡就能够进入艺术状态,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事实上我们要评判黄公望何以重要这样一个问题,必须把黄公望放在中国山水画史这几个转型期里、放在中国文人画发展的实际语境中去思考,才能探索出相对准确的线索。五代北宋以后,进入元代这个时期,恰好是中国山水画也是文人画的转折点,而在文人画经典图式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元代文人画与宋代文人画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宋代文人画提升的是一种文人余事,苏东坡的绘画就是一种文人墨戏,到了元代不再是文人余事,而是趋于一种较为专业的态势。事实上,在黄公望那里才把文人山水变成一种规范,一种可以传授、可以学习的东西,中国文人画到了文人山水画,变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具有规范性的绘画样式,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我想归结起来就是在元代以前,我们有过唐代的王维,有过宋代的苏轼等文人画的先驱,当时所谓文人画的创作只是文人余事,其技术、素养和表现能力尚不足以表达所有的题材,而且大多数画家都专注于竹、石、梅、兰等。到了后来有一个米氏云山,主要突出了水墨的氤氲,随机性很强,就是这种材质性、随机性的东西很难重复,所以米氏云山不好推广。到了文人山水画兴盛发展出现了“ 元四家” 之后,为我们建立了一种笔墨规范,笔墨技法变成一个丰富的系统,这样文人山水到此就确立了。在元四家当中,黄公望被置于首位,具有正宗流派的意义,不仅因为他是延续了董巨的脉络,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具有文人山水典范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黄公望的时候,看“ 元四家” 的时候,要看到他们在中国文人画,在中国山水画转型期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何以重要,或者说以何重要。
尚辉(《美术》杂志执行主编)认为:我们谈黄公望就离不开谈文人画,谈文人画也离不开谈董其昌的“ 南北宗论” ,事实上在学习文人绘画的过程中,黄公望是比其他诸家更为重要、也更为可学的一个对象。“ 南北宗论” 毫无疑问是董其昌等人在中国画史上提出的最具有理想色彩的理论,其虽然以禅喻画,但实际上是对唐宋以来开始形成的文人画进行了一次理论化的史学梳理和理论升华,“ 南北宗论” 的实质是董其昌对文人画理想的重构。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董其昌画学道路是从黄公望起步而上溯董源,从创作实践逐步上升到南北宗理论的认识,也就是对南北宗论的一种倡导。第二、董其昌确立了黄公望在“ 元季四家” 之中的首位。在元代时候赵孟頫的影响最大,王世贞所谓的“ 元季四家” 是指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四人。董其昌认为赵孟頫不仅是失去了中国文人气节问题,就是他的作品而言也不能放在元四家之中,所以董其昌就把赵孟頫改换为倪瓒,这样一来就把元四家之首的位置让给黄公望。这与他早年推崇和学习黄公望不无关系,在某种意义上黄公望应该是董其昌倡导南宗绘画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黄公望“ 以画为寄” 的人生态度,也更加符合他心目中重构的文人画理想。南北宗论重构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顿悟式的文人画创作心理结构,主要是赋予了文人画以敏锐的艺术直觉和独特的禅宗式的审美启悟,这是文人画理想重构的核心;二是强调以画为寄、以画为乐的创作目的和态度,凸显了绘画所独有的审美愉悦作用和绘画总体的审美价值;三是强调“ 以淡为宗” 的审美意趣,淡既出于自然性情,也离不开人文陶练。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黄公望不仅是董其昌研习画学的启蒙之师,而且在推崇南宗画学的审美观念也给于董其昌深刻的影响,并成为董其昌重构文人画理想重要画家人选和阐释文人画观念的重要依据。南北宗论的意义在于:南北宗论对于文人画理想的重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王维、苏轼等文人画提出、文人画理念的继承与重建,其重构性主要体现在对文人画史的重新认识与重新梳理。因而这种重构是对文人画理念的调整,是对文人画理想的对象化,是对文人画史的重组。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史实,而是通过理论重新构造历史,是带有一种虚构和想象的成份。所以“ 南北宗论” 开辟了师承文人画新的道路,开辟了文人画一个新的发展前景,从中可以看到黄公望对董其昌的影响,以及在南北宗论中的价值和地位。
尚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认为,现在黄公望的诗保存下来有二、三十首,都是在《元诗选》卷十二和卷十四里边,按照一般的记载黄公望是很有诗才的,可是他的诗集没有保存下来,也能够证明黄公望这个人诗的水平应该不太高。从那些诗来看,他的诗在当代绝对不是一流的,能到二流就不错了。可能是《元诗选》的编辑从画里边摘出来的,编辑者是一个挺爱画的人,这个事是一些资料里边有记载的,所以现在保存下来的所谓黄公望的诗,是不是都是真的?我想可能也有假的。
四、从富春山两岸实景到《富春山居图》:中国古代画家的师造化
余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认为:黄公望的山水画常常是以实景为题材,这个与元四家中的其他三家是有所不同,也是比较突出的一点。他的实景往往经过较大的艺术夸张,并不是刻画具体的某一处实景,这在他的立轴山水画当中尤其如此,有的实景直接以道教的活动有关,有一些则是他途径所见之地。比如他的《天池石壁图》,画的是苏州天池山的全景,实际上天池山的高度根本不像画面中那样高耸峻峭,是一片比较平缓的丘陵地貌。其实他这样画体现了他的一种透视的观念,我们过去比较注重是从右向左的栩栩展开,而在《天池石壁图》中则是由下至上的栩栩展开,前山和后山之间相互重叠、交错。另一幅《丹崖玉树图》与《天池石壁图》是非常相近的,而《九峰雪霁图》,是道教隐居炼丹的地方,描绘的是松江的九座道教名山,表达了这位全真教徒的虔敬之心。另外《九珠峰翠图》,也是有实景的,还有《富春大岭图》也是一幅立轴,事实上富春山的两岸没有这样陡峭的高山,完全是他把前后的山峦重叠而成的。再看《富春山居图》,其构图由右向左栩栩展开。在立轴的构图中,由下至上的散点透视造成山体拔高,对实景的描绘比较夸张,而手卷比立轴显然要真实得多。所以黄公望的《富春大岭图》跟富春山的实景有一些距离,而手卷《富春山居图》与富春山的实景更加接近一些。富春山这一地域的长度有100多里,应该是从桐庐的下面一直到富阳,黄公望画了不少与富春山实景有关的作品,有些作品不复存在了,但是在一些元代的文献里可以看到。黄公望作品的题目往往是其所画之地,取其景之大概,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景点,更要记住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的变化。黄公望所绘的《富春山居图》正是他实景山水画的绝顶之作,在此之前,更是为《富春山居图》的创作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综合体现画家的写生能力,这也反映出一个全真教徒晚年的生活— — 来往于大自然的山川之间。
张晴(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主任)论及《富春山居图》和黄公望的师造化时认为:第一,对景写生。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对景写生是非常严谨的,他在创作中非常重视把观照自然山川千变万化的心得和自己的创造融合起来。他的师造化是来自于“ 居” ,在“ 居” 的过程当中再去观察自然、体验自然、深化自然,是一种对景写生后的归纳和主观创造。第二,重视经营位置。黄公望从钱塘江到富春江,再到新安江,这一路绮丽的山山水水让他陶醉其中,《富春山居图》完美的结构布局和空间表现就是他多年的观察与写生的结果,他以平面横移的方式把几百里的山水景色展现在我们眼前,如同一个摄像机的镜头对着已经被剪切过的画面渐渐地移给我们欣赏。在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具体经营位置中,可以看到他把前山与后山之间的关系,安排的是如此自然真切。因此《富春山居图》虽然是黄公望在描绘实景的基础上创作的,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写生,而是在写生的基础上,对富春江两岸的山水形态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取舍。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中经营位置的独道之处在于,他不但考虑到作品整体的构图,也考虑到作品构图与观赏者之间发生的某种心理关系。第三,黄公望在表现语言上的精准。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中把长披麻皴可以说是用到了极致,我在1984年专门到钱塘江和再到新安江一带写生,一个月的时间把那里的山山水水走遍了,我发现富春江两岸的山体只有运用像黄公望这种长披麻皴才能精准地表达出来。事实上,我们从赵孟頫、黄公望、倪瓒的山水画和自然实景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清楚地发现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以各自独到的皴法来表现具体的山水质感,从中获得成功的美学传播。这正是中国古代画家在师造化的过程当中,在各自山水画样式表现和精神追求当中的心灵表现,关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从师造化到云游。黄公望尽管他出生于虞山却不是专门画那里的风景,从他在《富春山居图》的题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从师造化到云游的事实状况,因此黄公望师造化的特征就是“ 云游” 两个字,我们今天要用云游山水之间的心情来品赏《富春山居图》中的云游之意。
五、《富春山居图》的表现方式与黄公望艺术的当代意义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认为,黄公望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黄公望山水画的画法、画理和画格都值得当代中国画家借鉴、学习和反思,此处重点谈一下画格。画格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风格;一个是指格调。黄公望的笔墨风格在元四家中最丰富、最全面,很难用一个字来概括。如果说倪瓒的绘画风格可以用一个“ 简” 字概括,王蒙可以用一个“ 繁” 字概括,吴镇可以用一个“ 湿” 字概括,那么黄公望就不能用一个字概括,因为他是简繁、干湿并用,所以更倾向的画格是指绘画的格调,黄公望山水画的格调是雅、正、清、逸的。同时代的倪云林就说大痴画格超凡俗,指的是他绘画的格调,他还说黄子久之逸脉,就是逸品的脉,董其昌也说黄公望的画“ 神韵飘逸” ,王原祁评价他是“ 高逸” ,并认为是文人画的正传、正宗,但是究竟黄公望的山水画属于“ 神品” 还是“ 逸品” 是有区别的。董其昌说画家以神品为终极,事实上黄公望的画理和倪云林的画理是有所区别的,黄公望注重写真山之形,倪云林注重写胸中逸气,实际上黄公望的山水画是把真山之情与胸中逸气结合起来,形成了雅、正、清、逸的格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高雅的格调?王镛认为黄公望是基于他的深厚的文人修养,寄情山水特别是寄乐于画自黄公望开始,寄乐于画一种超功力的审美态度。倪瓒也说“ 能画大痴黄老子,与人无爱亦无憎” ,就是没有爱憎,不是说黄公望没有感情,而是说他的情感是超凡的、超脱世俗的。当代中国的山水画,很多格调不高,堕入邪、甜、俗、赖的乐趣,可能是因为画家的功利心太重,关心的是画的价格而不是画的格调。其实当代画家应该学习的是黄公望的学习方法,董其昌说:“ 黄子久学北苑,倪云林学北苑,各个不相似” ,所以当代画家学习前人无论是黄公望还是黄宾虹,都应该努力创造自己的面貌。
罗青(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认为: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是中国第一件“ 即兴修补呼应式” 的山水画,并对黄公望这张画做出两点表达和诠释。第一,《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七十九岁比较成熟的作品,是一个水墨写意画,这幅画并不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大制作,至少说依照水墨画的经验,如果经验老道一两个礼拜就可以画完,但为什么要画这么长时间?而且当无用师让他题字的时候,他为何还在题跋里说三、四年没有完备,还要留下来慢慢地画。在黄公望之前,水墨画是有相当的发展,有各式各样的画法,但是没有一个人像黄公望这样清楚地说明,他说画画要从淡墨开始画起,可改可救,他把“ 改” 和“ 救” 当做绘画的一个过程和部分,这是以前没有任何一个画家明确地说出来。事实上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特质,就是他提出了一个不断地修订,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可以互相呼应的一个山水画创作的过程。第二点,富春江既然是这样一个山水,我们用郭熙的方法来画也可以,用范宽的方法来画也可以,用任何方法画都可以,不必要画成黄公望的这个样子,可是黄公望就是很明显的有意识地要继承董源的。但是黄公望画的石头比董源还硬、还多、还大,跟董源的做法并不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发现黄公望引用董源的皴法,与宋朝大量引用典故的风气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仔细看,把黄公望的画放大以后发现他改动的非常明显,这真是所谓进行式的山水,就是永远在进行,这个进行式的山水,事实上黄公望本身就提出了他的理论,他说作画要随机应变,这个画是有生命力的,不断地在改变,你的笔墨之间也要配合重点的改变,使它产生一个复杂的交响,这个交响不但与自己心灵交响,同时也要充满了文化历史感与古人的交响。而这种不断修订的笔墨,到了清代王原祁那儿则发展为一种歪斜交错、来回犹豫不定的程式化图式表现习惯。
陈航(西南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在发言中指出:如果说从宋到元,中国画(尤其山水画)是从“ 形” 向“ 意” 的逐步升华的话,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则是表现这一升华成果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仅从笔墨上看便显示着中国画写意性物化表达的具体成果:其一是笔法的成熟。对于复杂的造化视像,从造型到万物间内在关系,笔法都实现了其最完善的物化层面的表达途径,使笔法成为了中国画语言的基础“ 语法” ,这一“ 语法” 甚至也实现了与中国画特殊工具(如毛笔)的完美结合。笔法具体表现为以线性笔墨为核心的笔的运动方式,即中侧交互、提按交互以及“ 正反弧” 线性交互(线体内外合一的S运动)的共同作用。笔法在绘画主体的艺术探索过程中成为由技入道的起点与途径,成为主体性灵传达的基本载体;其二,“ 达意” 的画境升华促成了“ 草稿之作” 的风尚与新的时代追求。宋代水墨山水画中以淡入浓的绘画基本方法在元代演绎为“ 不经意” 的水墨画稿“ 改本” ,笔墨的疏松错落与绘画主体无拘的精神游走相合一,形成了性灵与笔墨的契合与对应(这种方式的不断推演,最终产生出现代黄宾虹的艺术风格与高度);其三,这种“ 相合一” ,又进一步促成笔墨独立性的自觉,即笔墨表达此物之时亦在表达更为广泛的意义,于是非囿于一形之似,而更贵于不似之境,最终与非囿于一字之似的上乘书法相映照,并从本体上达成一致。于是越界便必然发生,对于书万象皆为“ 帖” ,对于画众书皆达物,也因此善书者每能画,善画者每能书。《富春山居图》所诞生的时代和所传达的艺术指向及其在后世来看所具有的特殊的转型意义,使该作品及其作者黄公望在画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认为,黄公望在通过他很独特的浑厚华滋形象特征来追逐他的内心,通过写生积累,通过他的一种对“ 理” 的追求来展开表现的一个过程。宋元之际,尤其是汉族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进入元代一个异族统治的现实状况中,在那样的处境和空间里所选择的人生立场、价值观与情绪是有很多的关系。确实,在一般情况下,元画的重理似乎是很难把理说清楚的,尤其对于汉族的知识分子而言。但是元画的重趣和后来明代重气的心学思想又是两回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元四家里边确实有相当多的重趣的追求,可为什么黄公望没有选择重趣,仍然是重理呢,这一点对于黄公望作为一个元代的画家,对当时存在问题的思考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黄公望在中年挫折、他对全真教的选择,以及他中年挫折以后开始选择山水画的学习和创作等,可能都跟他对于理的追求有很大的关系。很显然在文人绘画的发展历程当中,黄公望没有选择主观,而是选择相对客观(包含了主观元素的客观)的,所以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主观,这一点可能对我们理解黄公望的创作立场、他的想法、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点。另外,那种由淡到浓、不断地层层往上添加而营造出一个浑厚华滋的山水世界的创作方法,好像是永远处在一个捕捉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仿佛是不断对存在的一些叩问的创作方法。某种意义上说,有点儿像是后来的“ 行动绘画” 的概念。
六、《富春山居图》与《剩山图》的真伪考辨
单国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在发言中认为:《富春山居图》和《剩山图》合璧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当时被毁了以后还没有反映全部的内容,特别是最前边的部分到底发生什么,要了解其首段被烧毁的情况,还需要参照很多临摹本。《子明卷》和沈周临本,中间部分与《无用师卷》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而前面的部分就不一样了。《子明卷》的最前面画了一个小幅,然后是一个平台,跨过了河,再过来的山就是现在的《剩山图》这一部分。沈周临本基本跟《子明卷》差不多,前面是一个小幅,跨河是一个桥,平台过来就是一个高峰,就是现在看到的《剩山图》的这部分。最后结尾部分有很大的不同,《无用师卷》的最后是一片水域,《子明卷》就不是了,平滩上生出许多小树,而沈周临本最后也少了很多水域,大概是背临时简化了。事实上,经过分析《子明卷》和沈周临本都是根据《无用师卷》临摹的,那为什么前面不是“ 平沙五尺” ,说法不一样,甚至认为《子明卷》和沈周临本不是临摹现在的《无用师卷》,另外还有本子,这个参考有没有,到底前边那部分画的是什么,现在我就想解释一下,沈周这个本肯定临了是《无用师卷》之本,因为有沈周的题跋,谈到了收到以后又丢了,自己临的本子上也有题跋,因此,沈周临的绝对不会是另外一个本子。《子明卷》的起首,其长度到《剩山图》那个位置,跟《剩山图》的尺寸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它也有52厘米左右。按照乾隆时候的尺寸来算,一个尺相当于20厘米,被烧掉的“ 五尺” 可折算为117厘米,这还差了57厘米,这个差别的已经不是很大了。《子明卷》作为一个临摹本,很有可能把画面中很多平沙、很多空旷的地方给压缩了,而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于沈周临本中。从“ 尺寸” 跟“ 平沙” 这两个因素来分析,我们可以证明《子明卷》、沈周临本其原本就是现在的《无用师卷》之本,其中的部分就是被烧的部分。另外,就是很多著作记载《富春山居图》的时候,后面题跋的人不一样,一会儿这个人出来了,一会儿这个人又没有了,说明《富春山居图》有好几个本子,当然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再研究,但这不影响《子明卷》、沈周临本和《无用师卷》三本之间直接关系,我们根据《子明卷》和沈周临本同样可以了解到《富春山居图》的全貌。
许洪流(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在发言中对《剩山图》的真实性做出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并指出了关于鉴定《剩山图》的三个问题:一、《富春山居图》毁损了什么?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富春山居图》原来的长度。《无用师卷》目前总长度是636.9厘米,为完整的六张纸,每张纸的长度基本接近,平均长度是106.15厘米左右。参照恽寿平先生的记载烧焦部分还有两张纸,按照常理手卷和画卷一张纸不会特别短,当初烧毁之前的《富春山居图》的总长度应该是849.2厘米,即《无用师卷》的636.9厘米,再加上前面两张纸的长度。其次是关于烧毁的内容,最为重要的线索就是恽寿平《南田画跋》的记载:“ ……焚其起手一段。余因问卿从子问其起手处,写城楼睥睨一角,却作平沙。秃锋为之,极苍莽之致。平沙盖写富春江口出钱塘景也。自平沙五尺余以后,方起峰峦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余耳。” 已经烧毁的部分,一大块在浙江博物馆收藏的《剩山图》,那边是《无用师卷》的开始,在《剩山图》和《无用师卷》的衔接处就是“ 平沙五尺余” 。还有《富春山居图》原来的高度是多少。《无用师卷》的高度是33厘米,《剩山图》的高度是31.8厘米,问题是两图高度相差1.2厘米,《无用师卷》的高度是否少于未烧毁时的《富春山居图》?比较可能的原因是烧毁的时候手卷两端也烧焦了,《无用师卷》装裱的时候上下被裁切过,只不过上下被裁掉的内容没有《剩山图》多,这是比较正站得住脚一个解释。二、《剩山图》真伪的关键— — “ 吴之矩” 骑缝章。关于《剩山图》和《无用师卷》的骑缝章,是对它真伪鉴定的一个关键,我们来看一下吴其贞的《书画记》中说到的内容:“ ……今将前烧焦一纸揭下,仍五纸长三丈……为丹阳张范我所得……其图揭下烧焦纸尚存尺五六寸……今为予所得,名为《剩山图》。” 目前我们看到《剩山图》这个图章有一些倾斜,而《无用师卷》的图章也是略微有一点倾斜,并且倾斜度和《剩山图》完全在一条线上,假如说是后人买到了《剩山图》之后,没有《无用师卷》旁边做对子肯定不会对好,因此可以推测吴其贞在得到《剩山图》之前这个骑缝章就盖好了。三,质疑《剩山图》的“ 八不合” 成立吗?所谓“ 八不合” ,即1、纸色不一,2、墨色不同,3、山不相连,4、皴法不对,5、苔点不类,6、树木不同,7、小屋相异,8、水不能连。许洪流通过对《剩山图》、《无用师卷》、《子明卷》等不同本的具体内容进行了严谨的比较分析,认为对《剩山图》“ 八不合” 的质疑是不能成立的。
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首先回顾了《富春山居图》三个阶段的真伪论辩,第一阶段是乾隆皇帝鉴定《子明卷》为黄公望的真迹,而《无用师卷》被确定为假的;第二阶段是近几十年中,海峡两岸对已经确认为黄公望真本的《无用师卷》提出质疑,并对《富春山居图》火焚事情产生疑问;第三个阶段最终的结论是支持了《无用师卷》的真实性。另外,任平还说明了鉴定《富春山居图》应该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从乾隆皇帝鉴定的事情得出来的一个体会,就是鉴定一定要用作品说话,要以文献为依据,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要以某些权威尤其是帝王的权威为准绳。因为一旦掺入了政治因素,掺入了某种权威因素,往往判断就会失效。第二,美术作品真伪的考辨,不能光是注重于文字的著录,更要重视图像本身。图像与文字是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他们各自在鉴定过程当中各有优劣,各有长短,而美术作品的鉴定包括所有的细节、纸张的质量、笔墨、印章、装裱、时代特征、以及所有的题跋等。第三,图像考证在美术作品的鉴定当中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文字与图像的结合是今后要特别注意的。第四点,联系到《富春山居图》真伪的论辩,把它跟《兰亭》论辩一比较,就可以发现这两个论辩是中国文化史上面两大个案,同样都是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认为两岸所藏的《富春山居图》和《剩山图》都是真迹,二者的颜色是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才是对的,一个在故宫里保存得好,一个在民间保存得不好,在民间保存得不好就会发暗,如果《剩山图》发亮就错了,《富春山居图》在故宫保存得好一点就亮一点。
七、关于《写山水诀》、《快雪时晴图》、《富春山居图》画风及其他的研讨
李福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在关于黄公望《写山水诀》的绘画思想的发言中指出:黄公望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南画发展的过程中,黄公望引领文人画走向全面成熟,同时也为明清南画开辟了一个新的画格。黄公望提出的“ 作画大要,去邪、甜、俗、赖” 四个字,这不仅是黄公望的绘画主张,也是南画画格的精神或者是南画的指导原则,如果把这四个字的理解和解释都搞得很透彻,无疑是解开南画秘密的一个关键。“ 甜” 的对应面就是苦,是苦涩,艺术品的苦涩可以使观众感到有嚼头,有味道,可以回味。艺术家们如何避免作品的“ 甜” ,怎么样去“ 甜” ,李福顺认为只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才能够体会,才能够做到。“ 邪” ,就是有悖常理,扭曲变态,如元代饶自然《绘宗十二忌》中说:“ 一、布置迫塞;二、远近不分;三、山无气脉;四 、水无源流;五、境无夷险;六、路无出入;七、石止一面;八、树少四枝;九、人物伛偻;十、楼阁错杂;十一、滃淡失宜;十二、点染无法。” 等等,总之是失去了和谐,违背对立统一。“ 俗” ,画家最忌讳俗。黄庭坚曾经说过“ 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入耳。” 黄庭坚讲的是书法,书法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就为不俗,画如果过于简单,没有什么可回旋的余地,没有什么可捉摸的,平平淡淡就是俗了。“ 赖” ,用来形容人的一种心理状态,作为画而言就是不耐看、不吸引人。赖的反面是好,好就是要吸引人,要吸引人的作品就要有新意,无论内容或者形式,都是新颖的、耐看的。好的画要合理,所以黄公望说作画只是个“ 理” 字最要紧,《富春山居图》就是黄公望艺术主张最好的范本,是典型的南画。最后李福顺认为,黄公望提出的“ 邪、甜、俗、赖” 四个字,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王连起(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在发言中谈及黄公望《快雪时晴图》时认为:乾隆皇帝喜欢最好的三件书法叫《三希》,第一希就是《快雪时晴帖》,《快雪时晴帖》是王羲之65岁时所书,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当年赵子昂是见过的,真迹后边还有赵孟頫的题跋。于是他就放大临写了“ 快雪时晴” 四个大字送给黄公望,赵子昂临书是以貌取神,不像清代的碑学家们按图索骥。后来赵孟頫送给黄公望的“ 快雪时晴” 四个大字,就被装裱在黄公望《快雪时晴图》的最前面,而《快雪时晴图》,从画法上绝对是黄公望的真迹。事实上,黄公望是赵孟頫自己承认的学生,黄公望的绘画是通过赵孟頫改造过的董源、巨然的画法,这一点应该有一个交待。赵孟頫在于他把董源、巨然、李成、郭熙等都转变为文人的笔法,相传于不同的人,学习董源、巨然的有元四家特别是黄公望和王蒙,学习李成、郭熙的有唐棣、曹知白、朱德润等,在他们存世的画作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另外,王连起还提到董其昌南北宗问题,认为董其昌对赵孟頫是存有偏见的,在他的南宗系统里没有赵孟頫,北宗系统里也没有赵孟頫,但是当他提到元四家的时候,认为元四家都是有赖于赵孟頫提高绘画品格的,事实上还是承认赵孟頫对元四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王连起还说,元四家中吴镇是用墨见长,王蒙构图可繁可简,多种多样,倪云林只有简,王蒙会很多套路,而倪云林就是三拳加一腿,练来练去就是那几招,但是因为笔墨好,百看不厌,这一点也是他的特殊。而黄公望是兼而有之的。现在看到的黄公望的作品真迹,像《天池石壁》、《九峰雪霁》、《快雪时晴》等从画法、皴法变化多端,可见黄公望技法、面貌是很丰富的。黄公望的浅绛山水,就是经过赵孟頫改造的董源、巨然这类绘画,其《天池石壁》、《丹崖玉树》这种画法对清初“ 四王” 影响很大,而《九峰雪霁》、《快雪时晴》则更为精炼,所以黄公望确实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事实上他的《富春山居图》、《天池石壁》,已经让明清时期的文人画跳不出来了,由此可见,他在绘画史上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认为:黄公望的原籍是江苏常熟人,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不少文献都有记载。关于吴之矩,吴问卿的问题,事实上他不叫吴问卿,叫吴冏卿。为什么说吴冏卿对而吴问卿错了,因为名和字是相配的。邹之麟的题跋是问卿,应该是误写,还有一些人是根据邹之麟的记载也写问卿,所以冏卿是对的。再者“ 冏” 和“ 问” 差不多,有时候写错了,自己也默认了。对于火烧的问题陈传席认为是吴冏卿造的谣言,邹之麟的题跋没有提到,有可能是吴冏卿的侄子把《富春山居图》分成了三段卖钱了。另外,陈传席还认为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是董源、巨然的画风,而黄公望学习的是赵孟頫变化了的董源、巨然。赵孟頫把董源、巨然的皴擦变化成书法线条,像《鹊华秋色图》一样,后人看到这张画就认为董源、巨然就是这种画法,沈周也认为这是董源、巨然的画法。有人说《富春山居图》是学董源、巨然的,其实是学赵孟頫的,是通过赵孟頫学董源、巨然的。
(2011年5月21日李月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