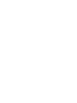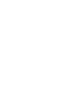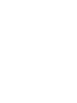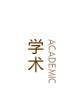学术讲座:我的父亲庞薰琹
2016-09-26 02:50:00来源:庞薰琹美术馆点击:9777
主讲人:庞绮(北京服装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庞薰琹美术馆名誉副馆长)
主 持: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孙磊
时 间:2016年9月26日9:30-11:30
地 点: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长清校区第一阶梯教室
庞薰琹美术馆根据录音整理
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1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我依然觉得就像昨天一样,他刚刚走,他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们脑海之中。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写父亲,我觉得很难提起这支笔,一个是因为自身的能力很困难,另一方面是感情上很困难,就像刚才我很不该在公共场合把这种情绪带给大家。所以至今为止,我没有写回忆我父亲的文章。但是我知道我应该写应该回忆,因为别的人是从其他角度来写父亲的,比如刘老师从学生的角度写,也有从同事、朋友这些角度写的,唯独我作为小女儿,作为家人去说庞薰琹,区别首先在于是家人,另外我们是最了解父亲生活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是别人看不到的,无法取代的。所以今天我也很感谢山东工艺美院给了我这样一次机会,就是让我从一个女儿的角度来谈谈父亲,特别是从生活的角度来讲。父亲晚年都是我跟着他,因为哥哥姐姐岁数大了,都出去了,都是我陪伴着他,在他身边,直至他去世。可以说我陪伴着他走完他的后半生。
父亲一生当中经历了两个非常痛苦的事情,第一个是反右,我们家庭碰到了家破人亡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文化大革命。因为年龄的原因,我没有经过反右,我跟父亲经历了文革,虽然我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印象深刻。文革期间我的父母被双双劳改,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进了单位里的牛棚,干着最脏的最累的活,虽然没有被打,但是受到了极大的人身侮辱,扫厕所,抬煤,清理垃圾等等这种脏活都是他们干。我在这个期间,每个月要做一件事,就是去他们单位给他们送粮票。为什么呢?因为当初是供给制,没有粮票,你这个月就没有饭吃,尽管我当时只有十几岁,但是我承担了这样一件事情。说实在的每个月去之前我都很纠结,只有这个期间我才能见到我的父母,平时见不到的,我当然希望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见到他们,但是我又很恐惧那种场面,很压抑很恐怖。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我去送粮票的时候,劳改队长正好在现场,他听说我要把粮票送给我父亲的时候,就去里面喊:“庞薰琹,你出来。”这个时候父亲就从那个门里走出来,我真的非常难过,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满身病痛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反右的时候他已经得了一身病,只见他戴着一个蓝色破帽子,穿着一身蓝布衣服,非常苍老,非常消瘦,走到我面前,我准备要把粮票给他的时候,听到一声大声的呵斥,劳改队长说:“你不能把这个粮票给他,你首先要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听到这话非常难受,我作为一个女儿怎么能对父亲说这种话,但是我不说的话,父亲拿不到这一个月的粮票,也就是这一个月都没有饭吃,所以我就带着哭腔,站在那里,说出了我这辈子最不该说的,也最不想说的一句话。他默默地看着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就被带走了。我那个时候心里真的非常非常难过,这就是我在文革期间所看到的,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其实他这辈子磨难多多,极其坎坷,生活从来没有愉快过。但是我当时只是个孩子,我并不知道,也不懂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只是作为一个小女儿照顾他,当时并不了解他的苦在哪里,直到今天我也到了不惑之年,我才开始真正懂得父亲究竟承受了什么。父亲在劳改的时候,早上八点钟要准时到传达室,跟着木工、瓦工一起学习,就在他清理垃圾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被扔到垃圾箱的作品,这件作品被他悄悄捡回家,后来被修复了,这件作品在1983年在中国美术馆被展出同时被收藏。我们看一下,这是他早年在法国留学时的照片,1925年他19岁去法国,其实年轻的时候蛮帅的;这是在成都;这是1951年;这是他老年。我记忆最深的是任何时候对着任何人,他都带着这种微笑,非常慈祥。60年代,这是在反右以后,他开始整理历代装饰画,那个时候,他从学校降级,一直降,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开始写《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这是他的一门课。这一张是文革期间,他在打扫厕所,从垃圾箱把自己的画捡回,最后经过修复,呈现这样一个面貌。
尽管父亲经历了很多很多坎坷,但作为家人来说,从没听过他的任何抱怨,什么攻击党,谩骂社会这种不满,或者是对他人的议论从没有过,他都是把苦难全部埋藏在心里。包括他的作品,特别的安静,特别的高雅,从来没有宣泄出不满的情绪。为什么我刚刚那么激动,其实就是看见父亲70年代的作品,他画画的情景都浮现在我的眼前。反右以后父亲分配到两间小住房,这两间住房的面积小到什么程度?总共面积加起来十四平方米,一间上午东晒,一间下午西晒,就是这样两间房,狭窄的地方要侧着身走,两三个人过来,房间就站不下了。我们家的一扇窗户和一个高温车间就是一墙之隔,高温车间白天不工作,晚上工作,我们晚上听到最多的就是这个车间用高音大喇叭播放样板戏,经常不能入睡,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居住环境下生活的。我们家最大的一个房间是哪里呢?是厨房,厨房成为我父亲画画的空间,当他画画的时候,连一个画架都撑不开,只能是把画框放到一个椅子上,人坐到小木凳上面,这就是他的画画空间。因为他已经被整,很多东西是不能画的,人不能画,风景不能画,其实不是不想画,但是由于很多客观原因他只能画花,我看到70年代早期我们看到他大量的花卉作品,这就是原因。他画的这些花是怎么来的呢?是别人送给他的,或者是从垃圾箱里捡到的这些花,他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过:“我把倒头烂叶的花画得美些,我相信生活会逐渐美好起来,我既然画画,总希望看我画的人,能感受到一点美好。”他也曾经写过这样一首小诗:“画既然画在画布上,就让你看的,我,中国人,活在21世纪,尽管一时乌云遮住太阳,被迫离开课堂艺坛,我想安静,想寻美,想寻找劳动后的乐趣,也想让你看见美,感受生活中仍有乐趣。”
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斗室里面蜗居了20多年,在这个斗室里完成了他《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的初稿,还创作了很多传世佳作。他的生活经历和作品是完全相反的,他的生活坎坷,饱经苦难,但是他的作品却是那么的干净、高雅,没有表现出过负面情绪,而今天许多青年艺术者,画面没有那么多的美感,处处宣泄出血腥、怨恨、不满的情绪。我们看一下70年代这些作品,创作之时我就站在旁边,现在看觉得非常熟悉,实际上画得就是那些倒头烂叶的花,但他画得那么美。在他生日的时候,也会画花来纪念生日,有几年的生日都是这样的。这些风景都是他以前的画稿,40年代写生的画稿。我来山东的时候,尤其是听到山东工艺美院的时候特别激动,我觉得特别亲切、感慨万分。距离现在40多年了,也就是1977年的时候,在这样的季节里,也是九月份,是我陪着父亲来山东,他还没有平反,他受到文化部文化局华君武的指示,来山东讲学、指导。父亲终于有了工作机会,完全不顾自己高龄病躯,到17个工厂,2个工艺美术公司,2个学校等等地方,其中也包括山东工艺美院的前身,工艺美校,去指导。他讲课的对象除了学生,还有工厂里的制作工人,在讲完课后,他问工人们听懂没有,工人们都特别的肯定,点头说听懂了,还有些没有听到课的工人都询问能否再次讲授,他深入工厂里和那些工人们,特别是制作者交谈,了解情况,回答问题。除了这些大量工作,还创作了许多水墨、油画、速写作品,可以说他在山东度过了非常愉快的44天,这44天他为他梦想的工艺美术事业辛苦工作,却非常愉快,在他离开山东的时候很多人来送行,很多人拉着他的手问他:“你是不是明年还能来?真的希望你明年还能回来。”
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他几乎眼泪都要下来了,因为他感觉到人们对他的尊重、尊敬。他说自己如何能无动于衷呢?所以山东之行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记忆,我们可以看下山东之行的作品。这一幅是画得烟台,是一幅油画,他非常喜欢大海,画了很多幅大海,但他没有说过为什么喜欢大海。我想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住的地方距离海非常近,当我还没起床的时候,他就跑到海边站在海边,长时间的去看海。我为什么要提山东之行呢,因为山东之行对他之后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们从这一点里,看到父亲对于中国工艺美术事业的拳拳之心,为这样一个梦想,他始终无怨无悔,矢志不渝的投入了大半生的心血。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才华横溢的画家,但是他为了中国的工艺美术事业,教育事业,牺牲了小我去成就大我。他身体力行的做设计,他在1941年就做出一套工艺美术集,里面都是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作品,衣食住行的用具,很实用很美观。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封面,这是一个油灯,他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点着煤油灯,在煤油灯下面设计了这些作品。这是他设计的陶瓷,还有壶、杯子、碗。他考虑到美观之外的功能性。根据他的图,我们也做出了实物,比较全面的来体现他的设计,像这个放毛笔的,包括尺寸,一根毛笔多长就设计多长。这个是一个化妆盒,这里是一盒一盒的,可以放些胭脂啊、散粉啊之类的,我们刚刚看到的都是漆器,这些是放水果的盘子。他还设计了一些布艺作品,这套东西是1941年设计的,现在看仍然不过时,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东西了仍不过时。包括这些纹样,他当时给学生讲授如何让运用传统纹样,学生非常茫然,不知如何去做,所以他亲自动手,给学生画了一套,他做出了很好的典范。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的增长,我才了解父亲究竟做了什么,有怎样的意义。有人评价我父亲说他像个基督徒,也有人说他像个佛教徒。实际上我的父亲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从我的感觉上说,他有某种宗教情节,如果没有这种情节,他怎么会有如此博大之爱?
有人曾经问过我你父亲晚年的时候,你一直在身边跟随,照顾,那么你是不是得到你父亲很多真传?我要谈谈我的经历,这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他本来不希望我学画,我是高中以后才开始学画,但是刚开始学习时挺痛苦的。我的父亲对我们采取的是“不教”式的教育,他从不告诉我什么该画什么不该画,从起形,调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完全凭感觉画,在我画不下去的时候我也曾拿着画去给父亲看,父亲从来没有指责过,他总是带着微笑说没什么,挺好的,你就画下去吧。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我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受了这么好的艺术熏陶,学画的条件太好了,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我个人的压力特别大,我的天资不够,但是出自这样的家庭,就当你画得不好的时候,会有人说,你是某某某的女儿,你怎么这样差啊?我的哥哥姐姐庞涛、庞均,艺术造诣都很高的,恰恰到了我这,给家庭抹黑了。我的压力特别大,但是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责备我,都是说看你自己,保持住你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一开始我都不理解,我总是想你为什么不上手帮我改一改呢?你上手改一改就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但是他从来没有帮我改过一笔画,到今天,我终于理解了父亲的“不教”是真正的在教你,他让你自己去悟。我开始理解了他这种教学方式,也开始用这种方法教我的学生。
从我进学校一直到我毕业,大家一定觉得我受到照顾,正好是这段时间父亲恢复原职,但是我跟别人没有任何区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我考了两年,而且别人都知道成绩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我去问父亲,你是不是能帮我问一问,这时候父亲带我去了学校,还让我站在学校门口,他一个人走进去,打听我的分数,出来后告诉我你的每一门分数是多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被中央工艺美院录取了。在我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仍然不知道自己被分去了哪里,父亲说有关庞绮的分配一切听从学校安排。其实他那个时候岁数大了,他想做一件事情,去完成《中国历代纹样史》的研究,但是他眼睛花了,手抖了,没有办法完成这样一件事,他想让我留在身边完成这件事。后来学校分派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分到哪里。我没有留校,回家之后跟父亲说,我分到了哪里去了。从我进学校到毕业,我甚至要比其他同学做的更多,我自己觉得我一定要低调,别人不知道我是谁最好,不能给父亲抹黑。虽然没有给我特殊照顾,身后也没有给我们留下财富,但是让我受益终身的,首先是这种人品,崇高的人格,伟大的人格。包括我的名字,“绮”,是美丽的丝绸,我经过两年的努力,考上中央工艺美院染织系,和我的名字,如此的符合,包括我后来所做的工作,第一我做了一个教设计的老师,第二,我做了父亲40年前去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的同样的工作,不知道是巧合的,还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我做了跟父亲同样的事情,我想这是对父亲最大的安慰。
这是父亲画的我大二时候的一张像,早在40年代的时候,他就做了收集工作,他本想编一个历代装饰画研究,做了大量收集工作,从彩陶时期到清代,他曾经有很好的条件,就是他曾经在中央博物院跟着梁思成、梁思永这些大学者们工作过,所以他亲眼见到过很多文物,他将这些文物上的图案一笔笔画出来,一共有几十本这样的东西。他收集购买了三百多件少数民族服装,由南京博物院转交给故宫,现在还收藏在故宫。这是80年代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他写的前言语言都很朴素,但是能让你思考一些东西。70多岁高龄的时候,他到了敦煌,为了他的历代装饰画研究重做修改,稿子已经送到了出版社,又拿回来。70年代敦煌的条件非常差,但他仍然在洞窟里写写画画。
作为家人,我们对怀念父亲从感情来说是不容置疑的,为什么要在这里纪念庞薰琹,不仅仅是家人的感情,我们也应该像父亲一样放弃小我成就大我。他不仅仅是我们的家人,他是国家的,是民族的,甚至是世界的。我们在怀念他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学习他的精神,这种精神就像武术一样,当我们传授武术的时候是要强调一种宗师精神的,有了这样一种宗师精神,才有灵魂,所以特别是当下,我们学习艺术、学习设计的青年人应该更多的去了解庞薰琹,他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有了这样的梦想,一直在为梦想不遗余力的奋斗,所以他的一生是探索探索再探索的一生。我们要学习的不仅是他的技巧风格,我们更要学习的是他的精神,特别是年轻人,希望在你们身上,传承是靠年轻人的,所以希望年轻人能继承老先生的思想,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而传承。不仅我应该怀念自己的父亲,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永远缅怀他。